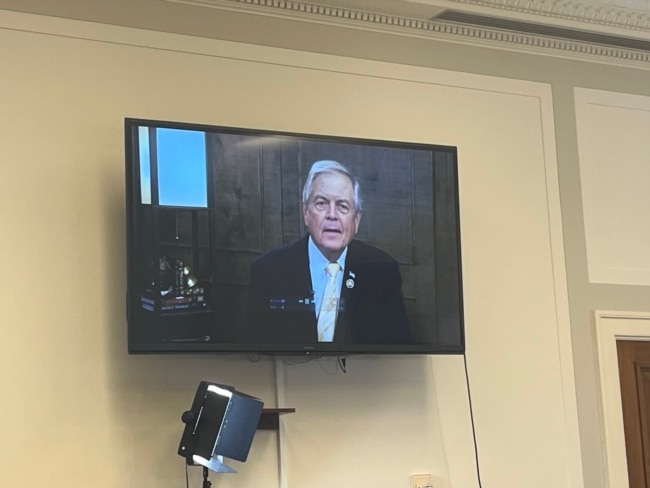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五○年代北京朝陽門外東大橋芳草地,是全國文聯宿舍所在。一大片簡陋的紅磚平房,分成若干小院落,組成一個大院落,像棋盤一樣。大院北邊有一個傳達室,統稱“芳草地五號”。每小院內,一排八間平房,每間只有十二、三平方米,單身者住一間,有家小或老人的占兩間。每小院有一廁所,為公用。平房階前為黃泥地,是夏日乘涼或種蔥蒜的活動餘地。所有小院都是一個格式。那時的朝外,冷落、荒涼,名為“芳草地”卻無綠茵,倒有一股鄉間氣息。五號雖是宿舍大院,但送煤、送菜小販都可自由出入。每小院前後緊挨,院外左右是道路。這個大院,文聯各協會的文藝家們多住在此,例如油畫家倪貽德,“胡風分子”主將路翎,左派戲劇家屠岸,曲藝界領導人陶鈍,評論家戴不凡等等。
芳草地五號靠中一排的十院,八間房中住著陳朗等六戶人家,一九五七年反右鬥爭中,六家中三家是右派。後來歷經階級鬥爭的深入,芳草地五號各院住戶,陸續地不少劃入“黑五類”份子的範圍了。 (博讯 boxun.com)
張郁住在靠右邊一排院落某院,在陶鈍院之前,路翎院、唐湜院之後。他是四川人,出道較早,到劇協之前當過報人、記者,性格活潑熱情,愛交際,愛戲劇,尤愛川劇,相當自許。一九五七年“鳴放”,“幫助共產黨整風”,幫助過多了,秋後算賬,如張郁其人自然是甕中之鱉!我在一九五九年離開福建到北京,與陳朗同住芳草地五號十院,因屬右派,是孤立的。平日來往也是右派,不敢公然交往,影影綽綽,避人眼目。張郁都是夜間來我們家。那時反右斗爭已勝利結束,全國揪出的右派份子據說有百萬之多,文聯各協會所定右派,部分已“先遣”入監或遣送邊遠勞改,其他大多尚在等待處理,前途未卜,人心不定。張郁尤見憂愁,因為他的妻子,川劇名演員楊淑英提出要和他離婚。楊身為共產黨員、川劇院院長,本來嘛,張郁既是四川同鄉,又是全國劇協大編輯,是川劇的鑒賞者,楊淑英表演藝術的吹鼓手,玉種藍田,門當戶對。但是張郁劃成右派了,四川省領導不能讓四川省的名家有一個右派丈夫,不能在政治上沾污共產黨要培養的紅人。是一定要楊淑英離婚的,楊淑英從小學藝,出身貧寒,“根子”正,是提拔對象。她沒有多少文化,談不上遠見卓識,經不起政治壓力及地位的誘惑。她一次次從四川趕到北京,他們新婚不久,還來不及調到一起,她要來面議離婚。但每次都以“抱頭痛哭、情意更深”而分別!夜深時,張郁向我們訴苦,滿面的焦慮與無奈,但是他對楊淑英只有理解,沒有怨言。他時又患腰痛,似乎忽然衰老了。
時在“大躍進”、“大煉鋼鐵”,文聯在懷來(桑乾河畔)設有勞動基地,各協(劇協、音協、美協、曲藝等等)輪調一般幹部到那裡名曰“勞動鍛練”,而定性的右派們也調入其中,名曰“勞動改造”,受所謂貧下中農和無冕同志的監督,實際上是受後者的監督,餓肚子的老鄉哪裡管得著這許多。張郁和陳朗們也都先安頓在這一基地,等待再處理。對右派份子的處理,漸次展開,這是從一九五八年春天對極右份子驅送北大荒以來的繼續。後我們一家發遣甘肅,於是變買家俱,分贈古董,束裝遠行,這是我們今後二十多年每況愈下的第一步。目的地是甘肅蘭州。六○年代初期正是路有餓殍的時期。陳朗分在甘肅省文化局戲研會工作。他曾從文化局分回一小袋土豆,在大街上被人搶了。十月的蘭州,已經下雪,據說在春天,不僅像北京一樣風沙滿天,還要落土。我們到了蘭州約二個月後,張郁亦從北京被驅遣到了省文化局。我們又在賢後街一個院落裡相聚,真是“人生何處不相逢”呵!他仍然抑鬱寡歡,最先告訴我們的消息是與楊淑英終於離婚了。在蘭州只過了一個月,他想回成都去,提出辭職。當時的形勢,對“辭職”一說,大家不可理解,無法接受,真乃“爹親娘親不如黨親”,怎麼可以離開“組織”,脫離“組織”?否則一個人不就沒有前途和沒有活路了嗎?但在那個年頭,誰又顧得了誰?張郁一走,再也沒有音訊。
過了漫長的顛沛的二十年後,直到一九七九年底和次年初,右派“改正”,張郁像出土文物一樣,又冒出來了,他又回到了北京,參加文化部舉辦全國戲曲會演的會刊編輯。陳朗比他僅早數天,已從甘肅西部農場經蘭州返北京。二人又成了同事。接著劇協體制恢復,二人均回到劇協。
廿年不見,張郁還不見老,然仍孑然一身。他說這廿年以來,雖然在“文革”中吃了不少苦頭,但學會了木匠活,成了當地小有名氣的“張木匠”。他笑著對我們說:“待你女兒出嫁,我親自為她們做家俱。”
約一九八五年夏,我們在杭州老家,張郁因出差之便到杭州看我們。我的居所是舊屋、閣樓,但是很雅致,簾籠低垂,頑石生煙,時花滿座,張郁很贊美。我們請他到龍井飲茶。他對西湖,對龍井的幽深林密都極欣賞,他讓我們代購兩斤上好的龍井名茶為楊淑英寄去。談到楊淑英廿年以來對他,無論是經濟上、精神上仍都支持,她的子女亦待他如同親爹。楊與後夫感情不好,落實右派政策後,他曾想過破鏡重圓,但終屬不可能。
一九八六年,我為張郁介紹了我們的朋友施美玲,覺得他倆可以互相扶持走完人生這條道路。小施是個孤女,年輕時戀愛受挫,一直覺得沒有好男人,故而一直單身。她護士出身,四十歲,有些漂亮,有些情致,喜歡與三五良朋品茗賞景,喜歡聽蘇州評彈,情性溫厚,但身體多病,長年患高血壓。張郁看了她的照片,經過我的口頭介紹,覺得他們倆人可以作進一步的交流,因工作忙,先兩地通訊。這本來是件好事,如果“好事”終於因為“多磨”而成功倒也罷了,通訊後不久,不料小施忽然摔了一跤,竟中風臥床了。張郁想整理一下手頭工作,南下探望。他先匯來數百元錢,然後是兩封長信,備極安慰,說是安排她進京治療,將遍訪天下名醫,為她妙手回春。信寫得真摯感人,不相信是五十多歲的男人手寫。他還說“即使她終生臥床,也不以為累贅”云云,還設想了他們以後共同生活的情況。
但施美玲畢竟未及等到張郁來面見她,就去世了。醫院的護士說她“死得很快樂”,頭一天她還好好的,來了一位廣州朋友,為她洗頭,為她燒了些可口的菜餚,一起看什麼信件,朋友到晚上才離去,臨走前還一起唱歌呢!可是她就在這天午夜突然地,悄悄地死了。我不能明白她那天的心情,但護士們都說“她很快樂”!
一直到一九九○年,張郁與武漢一位歌唱家結婚了,我常常在北京,因逗留時間短暫,我始終未見著這位歌唱家,但據說是色藝雙全。張郁是多情種子,他歷經患難,必然珍惜,我祝福他們地久天長!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