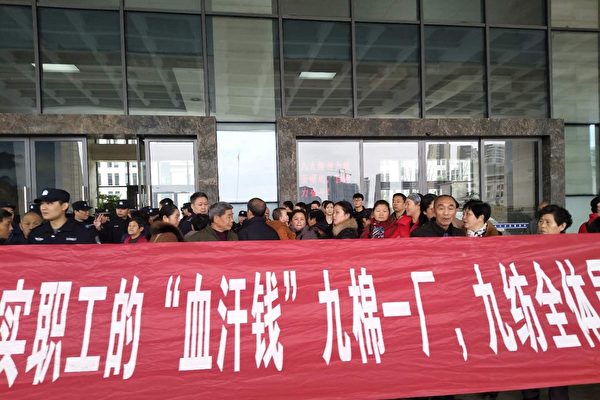刘增云转自博讯网: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在我的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诗篇》二十三章
民国时代著名的政论杂志《观察》的主编、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储安平,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言简意赅的话:在国民党的统治下,自由是多与少的问题;在共产党的统治下,自由是有和无的问题。两大政党的不同,在此一览无余。这里所说的自由,至少应当包括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所提出的表达自由、信仰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和免于匮乏的自由这“四大自由”。
公民是否拥有宗教信仰自由,是判断一个国家是否为“文明国家”的标志之一。作为一个国际性的人权概念,宗教信仰自由是在二十世纪中期产生的,最初正式提出这个新概念的是美国总统罗斯福。一九四一年,罗斯福在美国国会上建议成立联合国的发言中,提出了“四大自由”的说法,其中便包括“信仰自由”。而现代的宗教自由的定义的基础是《世界人权宣言》的第十八条: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以教义、实践、礼拜和戒律表示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作为一份条约性的文件,它在每一个签署国都具有法律地位。因此,现代的宗教自由是一个法律概念。这个概念根源于民权与神权的分离:一个国家管理社会的总体,但它不介入每个人的信仰和政治观念,它保障每个人建立自己的世界观的权利。1就国际法的层面上来看,中共政权接受了该宣言,理应遵守之。
然而,正如储安平对中共本质的一针见血的剖析,中共建政之后对民众的自由与人权的剥夺,超越了此前中国所有的政权。中共当局一方面大肆实施无神论的教育和宣传,另一方面努力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缔造成一种全民迷信。在毛泽东时代,宗教信仰自由成为受到戕害最为严重的公民权利,包括基督徒在内的各宗教信仰者群体,成为被包含在“地富反坏右”之中的、隐形的贱民阶层。研究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历史的学者指出:“虽然中共在其伪宪法上标榜人民有所谓的宗教信仰自由,但基本上它是一个无神论政权,因此对宗教先强调人民更有不信的自由,进而以惨酷的手段对信仰作种种迫害和摧残,于是基督教在中国面临了重大浩劫。中国基督教这棵有百余年历史之树,在共产主义的狂风暴雨的无情打击下,几至连根被拔起,奄奄一息,状至凄惨,其惨状比庚子之难更甚百倍。”2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中共大量修建监狱和劳改营,将数千万没有资格进入新时代的民众关押其中,强迫劳动、洗脑甚至折磨至死。
在中国黑暗的“古拉格群岛”中,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不愿放弃信仰的基督徒。经过中共持续的、残酷的宗教迫害,从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中国基督徒的数量迅速下降。无庸讳言,相当一部分信徒,或者半推半就地与官方“三自运动”合作,或者干脆就放弃了信仰。但是,仍然有一群置生死于度外的圣徒,穿越了毛泽东时代死荫的幽谷,跑尽了当跑的路,守住了所信的道,打完了美好的仗。他们是劳改营中奇迹般的幸存者,人数虽然不多,却如同光和盐一般,改变了这个世界的结构。他们的生命见证,可谓荣神益人;他们本人,亦成为福音的种子。这群忠心的仆人的存在,是八十年代之后基督信仰在中国复兴的前提。俞崇恩、李慕圣、林淬峰便是其中三位受苦的前辈,他们因受苦而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被捕缘由及劳改时间
以俞崇恩、李慕圣、林淬峰这三位基督徒为例,他们都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或者是愿意为社会服务的专业人士,或者是不问政治的全职传道人。然而,他们并未犯罪却被逮捕入狱,受尽虐待并被强制劳改。他们个人的基督信仰、传福音的言行以及不认同“三自运动”的立场,都成为当局眼中不可饶恕的“严重罪行”,因而被剥夺自由及政治权利长达二十年左右。中共建政之后的每一次政治运动,如“三反五反”、“反右”、“文革”和“清除精神污染”等,均有其针对的主要对象和阶层,但基督徒群体无一例外地都是被打击的对象之一。
俞崇恩出生于基督徒家庭,其父是著名的基督徒及翻译家俞成华。一九五六年,中共官方开始大规模打压全国各地的独立教会,俞崇恩所属的教派“聚会处”亦首当其冲。当时,他被当作“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集团青年骨干分子”和“集团首恶分子”在苏州的代理人,白天继续担任中学教师,晚上到公安局“交待问题”。由于他并没有犯法,只是拒绝参加“三自”,属于思想问题,按照当时的政策,并没有被逮捕。到了一九五八年五月“反右”后期,他才被当作“反革命分子”抓捕入狱,押送劳改农场。该案件并未经过法院的审理,他也没有具体的刑期,承受的几乎就是无期徒刑。此后,俞崇恩辗转若干个劳改农场之间。
一九六二年和一九六三年,俞崇恩在劳改农场暗中传福音被告发,被连续批斗两个冬天。一九六五年“文革”前夕,劳改农场的领导宣布继续给他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一九七四年,在被“改造”十七年之后,农场的干部找他谈话,劝诱其放弃信仰。他针锋相对地回答说:“我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为着我所信的主耶稣,可以不惜一切。”3他因而成为极少数“没有改造好”的囚徒,又被关押了五年时间。在此期间,他没有工资,没有节假日,在任何方面都低人一等。直到一九七九年,他才被释放回家,而所谓的“平反”则迟至一九八七年。也就是说,俞崇恩被强迫劳改长达二十一年,真正恢复公民身份则是在二十九年之后,那时他已经移民美国。
李慕圣也出生于基督徒家庭,他毕业于中国神学院,是一名全职的传道人。一九六零年,他被拘捕时,当局并没有给出任何罪名,连劳改队长也感到奇怪,问他说:“你没有犯罪、也没有犯错,那你怎么会到我们这里来呢?”他回答说:“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后来,队长又问:“你还信不信耶稣啊?”“信!”“那么,我再问你,你传不传耶稣?”“如果有可能,我还要传!”“哼!这就是你的罪状,你准备去好好的思想改造吧!”4就这样,李慕圣开始了第一段牢狱生涯:从一九六零年至一九七零年,整整十年时间。他先后被关押在看守所、监狱和劳改营等各处。
一九七零年被释放之后,当局不允许李慕圣从事任何工作,强迫他参加挖防空洞的劳动。即便在“文革”的高压下,他仍然坚持传福音,并在上海西郊建立聚会点。一九七三年,他因为“搞宗教活动,导致当地出现宗教狂热”,被便衣绑架、逮捕、严刑逼供,最后被判处死刑。一九七五年,他被从上海押回河南老家,当局计划在河南将其处死,以减缓外界的反弹。不久,四人帮垮台,中国政局出现转机,他的死刑被搁置。一九七九年,审判官来到牢里,拿着一张纸对他宣布说:“我代表中央人民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你宣布:对你实行无罪释放。”5法律竟然可以翻云覆雨,这究竟是庄严的宣告,还是拙劣的把戏?当事人并没有获得当局的道歉和赔偿,实施迫害一方仍然扮演恩人的角色。出狱之后,李慕圣从未停止过传福音的步伐。八十年代以来,他因积极参与传教活动,多次被当局拘押、传讯和监视居住。
与俞、李二人不同,林淬峰并不是全职传道人,而只是一名普通的平信徒。在中共建政之初,出于对“新中国”的幻想,他毅然从香港返回大陆,为新政权服务,任职于交通部航道管理局。一九五五年,因参加王明道的教会并反对“三自运动”,以反革命罪被捕。一九五七年,免于起诉而释放。6被释放后,林淬峰坚持参加家庭聚会,并表示:“政府逮捕我是逼迫教徒,我不是反革命。”他建议家庭教会“化整为零”,鼓励教徒“要刚强,不能软弱”。当局搜集到这些言行,他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表面上看,与俞、李相比,林淬峰经历了更加严格的司法程序,被正式判刑——判刑的理由今天看来无比荒诞。即便如此,直到一九五九年,在看守所被关押一年之后,他才接到法院发给的一纸判决书,“我以为队我判决也得在法院郑重其事地进行吧,原来是人不知鬼不觉地草草地把一张纸塞给我,我以后十八年岁月就这样交待了”。7中共当局任意践踏法治的行径简直令人发指。
一九七四年,林淬峰在劳改十六年之后被“提前释放”,然后被安置在北京市劳改局辖下在天津地区的茶淀清河农场就业。在这里,他是一名“准囚犯”,直到一九八一年离开中国大陆为止。他将清河农场称为“当代的奴隶庄园”,并一针见血地指出“留场就业”政策的实质便在于:“当代的奴隶庄园所奴役的是称为国家公民的‘自由人’——劳改释放犯,他们没有人身自由,没有选择职业的自由,没有行动的自由,而只有自由在政府强迫的劳动下被藐视、被剥削。他们和在农场里服刑的犯人其实差别仅在生活上好一些,相对的在农场范围内自由度大一些,而劳动量和劳动性质却是一样的。”8这种空前绝后的“留场就业”政策,使得囚徒们“一日为囚,终生为囚”。前前后后加起来,林淬峰失去自由的时间长达二十六年。当他一九八一年重返香港的时候,一生中最宝贵的三十年光阴已经过去了。
从这三位基督徒的遭遇可以看出,他们根本没有任何犯罪的事实,他们对新政权完全是无害的人,他们仅仅是不愿放弃个人信仰、不愿归属“三自运动”,便成为罪不可赦的反革命分子。信仰问题成为政治问题,始作俑者乃是中共当局。信仰与政治发生关联,是当代中国无法回避的现实。因为,在中共当局的眼里,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也要归凯撒,他们要粗暴地介入社会生活乃至个人心灵世界的所有领域。一个用暴力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政权,已经自我取消了其权力的神圣来源。毫无疑问,对这样的政权进行置疑和批判,乃是信仰者捍卫自身信仰自由的第一步。
抵制“三自”运动居然成为一个重大的罪名。由此可见,“三自运动”是中共当局用以控制教会、迫害教会、乃至消灭教会的工具。“三自运动”的基本原则和运作模式,完全不符合圣经的真理,亦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和普世的宗教信仰自由原则。显然,“三自运动”的属下没有一个是耶稣基督的真教会,他们虽然窃据了教堂,但他们只是橱窗、稗子和假冒为善者。
昔日,先辈们宣称,“圣经的原则必须持守,不可妥协,在原则上,尤其基本原则上妥协,就失去见证,得罪神”9,他们不惜为此坐牢甚至赴死;今天,当局的逼迫有所收敛,却有若干海内外的教会、机构和信徒,以能与势力庞大的“三自”系统合作为荣,他们忘记了:任何企图与“三自运动”妥协、合作、并存的想法及举措,都是对纯正信仰的亵渎与背叛。
监狱和劳改营中的苦役与饥饿
在二十世纪人类的历史上,纳粹德国、苏联和中共是将集中营制度推行到极致的、最大的三个极权政府。其中,“劳改营”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集中营,这一制度最为隐蔽(虽然“劳改”一词经由人权活动家吴宏达及其创立的劳改基金会的努力,已经进入了英文、德文等词典,但相对于纳粹集中营、大屠杀及苏联的古拉格这些早已家喻户晓的名词与事件来,“劳改”及其所代表的一整套政治迫害制度,在信息自由的西方仍未广为人知,在信息遭到官方封锁的中国更是处于一种“潜话语”的状态);另一方面,这一制度持续的时间之长、波及的人数之多和遍及的地域之广,也是当仁不让地居于首位(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之下,中共当局虽然不再公开使用臭名昭著的“劳改”一词,但整个劳改系统仍然在有条不紊地运作,甚至变得更加成熟和精密)。
在劳改营中度过漫漫岁月、乃至失去生命的中国基督徒的人数,迄今为止仍然是一个谜。这个数字与大饥荒和“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一样,让历史学家们望洋兴叹、瞎子摸象。但是,如果研究二十世纪中国的教会史和基督教的传播史,便不能不关注这些受难的信徒;展望未来基督信仰在中国的复兴,亦必须激活受难的先辈留下的美好见证。虽然勾勒出整个基督徒受难的图景尚存在相当的困难,但今天我们可以通过少数幸存者只言片语的回忆和讲述,展开一些微观的分析与评述。
一些珍贵的历史材料逐渐浮出水面。在远志明及其神州传播机构拍摄的纪录片《十字架》中,可以发现若干位坚持信仰而入狱二十年左右的先贤的音容笑貌,可以看到他们历尽沧桑之后痴心不改、坚如磐石的信仰,可以听到他们平淡从容的、没有怨恨而只有爱的娓娓讲述。与他们相似,如果以世俗的观点来看,俞崇恩、李慕圣、林淬峰等人都是不幸的,他们最宝贵的青春岁月全都在劳改营中消耗掉了;但是,如果以信仰者的立场来看,以三位基督徒为代表的为义受苦的前辈又是幸运的,他们九死一生,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却没有遭害。在重新获得自由之后,他们继续传福音的工作,并通过传记和自传,将那段可怕的经历记载下来,激励无数选择了“进窄门”的弟兄姊妹。
俞崇恩被关押的条件最恶劣的一个地方,是位于闽北山区的劳改营。从上海到闽北,简直就是从现代世界跌入中古世界,那里没有一丝文明的气息,人们像鲁宾逊一样赤裸裸地面对大自然严峻的考验:“劳改营位于闽北高山区的半原始森林,先后被押送来的两万人,没有住的地方,连帐篷也没有,必须白手起家,建造劳改营房。……那里是个靠海的半原始森林,每年都有十几次台风。在夏季,每周都有雷阵雨,在我们还未盖好简陋茅舍之前,大约半年光景,每当风雨来临,只要几分钟时间,所有的行李都湿透了。”10显然,这是当局有意的安排,他们是在“借刀杀人”,这把“刀”便是恶劣的自然环境。
劳改农场管理当局肆意虐待囚徒,强迫所有人从事强体力劳动,即便瘟疫横行的时候,也不放松压迫。再加之毛泽东强行推行错误的经济政策造成全国性的空前的大饥荒,劳改营的囚徒们普遍忍受着饥饿的折磨和劳动的压力,死亡的阴影笼罩在每一个头上。俞崇恩回忆说:“在闽北期间没有吃饱过一顿饭,从岁首到年终都是一样,连半饱也没有,无论过年过节都是一样吃不饱。……死去的人很多,尤其是体力强壮的人先死,因为他们吃的东西和我们差不多,而付出的劳力却比我们多得多;由于入不敷出,所以体力耗尽,提前死去,有的劳改队,尤其是靠山顶的,气温甚低,大部分的人都死去了。”11当时,人们的身体状况清晰地表露在脸上,人们一看对方的脸上便能揣测出他还可以活几天,一照镜子也能估计到自己的寿命还有多长。
当局从来不会在意劳改犯的死亡,默许甚至暗中鼓励死亡的蔓延。那些死亡人数最高的劳改营的管理者,不仅不会收到谴责,反倒迅速获得升迁的机会。在大饥荒和历次政治运动中,数千万普通的老百姓失去了他们的生命,对于毛泽东和统治阶层来说,无辜的生命只是一串串空洞的统计数字。被划入“敌对阶级”行列的囚徒们,既然在政治生命上被宣布“死亡”了,那么肉体生命的死亡自然就无足轻重了。在俞崇恩的回忆录中,两次提及劳改农场的死亡人数,第一处是:“到一九六二年劳改营迁到安徽时为止,在四年里,半数以上的人已死了。”12第二处是:“当时整个闽北上海劳改局农场全部迁到安徽宣城乡下,改名为上海市劳改局天湖农场。……当我们离开上海市劳改局闽北农场(我被编在坑塘分场)时,我场已经死了一大半,二万人只剩下八千多。”13接近百分之六十的死亡率,令某些纳粹集中营也望尘莫及。与中共的凶残相比,希姆莱之流真是“过于仁慈”了,他们真应该到中国来“取经”。
在李慕圣的传记中,也提及劳改营中极其险恶的环境和极高的死亡率。第一次入狱之后,他与其他四百位犯人被送往安徽的一座矿山。“才到矿区,犯人们立刻就被编成小组。一组负责挖矿,另一组则把挖出来的矿石装上板车,拉到一公里外的山坡上;那里有传送带,可将矿石运送下山,以便装上轮船运走。工作每天采取三班制,上工八小时内,一定得拉满十二车的矿石,即使雪深、冰厚,任务完不成,也绝不准下山休息。虽然工作繁重,但每天只供应两餐,每餐只有一碗半,是小块番薯加一点野菜煮在一起的。很多犯人埋尸矿山,他们当中常是因为任务完成不了,又过了吃饭时间,体力不支昏倒后,无人理会而死亡。”14由此可见,死亡不是无法避免的,而是当局故意造成的。
在那里,李慕圣所受的待遇比一般人更为严酷。因为他是思想犯,没有一定的刑期,这种“危险分子”,被安排在矿区地势最高处劳动。他每天必须爬更高的山,挖最难挖的矿。当局认为藉着这种随时可以让他送命的劳动,可以使他知难而悔悟,甘愿放弃原先坚持的信仰。15据李慕圣观察,这所矿山吞噬了大部分难友的生命,管理当局从未采取积极的措施来遏制囚徒批量死亡的状况。这本传记中清楚地记载说:“劳改队里视人命如草芥,短短的时间里,与慕圣同去的四百名犯人,只剩下了一百二十人。”16这个劳改营的死亡率居然高达百分之七十!
由于地处“天子脚下”,林淬峰的待遇明显好于俞、李,他所在的监狱和劳改营中没有出现囚犯大批死亡的情况。但是,饥饿是所有的监狱和劳改营中普遍存在的事实,恶劣的食物更是触目惊心。在自传中,林淬峰用了很大的篇幅来描述狱中的各种食物。狱中常吃的是一种变质的绿色窝窝头,“这窝窝头从伙房抬出来,老远就闻到一股刺鼻的辣味,咽下去后喉头苦苦辣辣的,呛嗓子。看着像发霉的绿色,哪有粮食的味道?……这里面含有大量的致癌物质,但是谁都不敢说。”17还有一种粱米面粥,“吃的时候很顺嘴,可是吃到肚子里,到达大肠就把大肠里的水分都吸干,拉不出大便,这可苦了。……医务所每天派人来给拉不出屎的犯人喝一大杯粉红色的药水,大便才畅通,幸亏只吃了一个多月,总算熬过了这一关”。18囚徒们经常食用的还有白菜帮子、窝窝头等最为低劣的食品。即便这些食物,其数量也不足以填饱肚子。
对照这三位基督徒的回忆,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中共的劳改营环境恶劣,饥饿和疾病肆虐,死亡率极高。劳改营是中共消灭异己分子的重要手段。若不是靠着上帝的保守和上帝的恩典,这些基督徒根本不可能幸存下来。
抵制洗脑,坚守信仰
中共当局以“劳改营”命名其集中营,其实这一命名并不准确,它仅仅标识了“劳动改造”这一侧面——所有的劳改营中,囚徒都被强制从事各种艰苦的体力劳动,这些劳动会对劳动者的身体健康造成致命伤害,而且基本上得不到任何报酬。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当局认为,囚犯不再是具有独立人格的生命个体,劳动是对囚犯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实施改造的必要途径。他们不仅重视囚犯的劳动所创造丰厚的经济价值,更将劳动作为对囚犯的一种严厉的惩罚措施。
在中共的劳改营中,除了长时间的、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之外,“洗脑”也是囚徒们必须承担的一项苦役。劳改营不仅是“劳改营”,而且还是“洗脑营”。囚徒们不仅被剥夺了身体的自由,而且还被剥夺了心灵的自由、思想的自由和人格的尊严。劳改管理方组织囚徒学习中共的教条和政策、毛的著作等,并要求讲述或撰写“心得体会”。当局还号召囚徒之间互相揭发和批判,以囚犯整囚犯的方法早已炉火纯青。许多在劳改营中生活过的囚犯声称,在如此严峻的环境下,只能不再将自己当作“人”来看待,只能遵循残酷野蛮的丛林法则,为了能生存下来,任何卑劣的事情都可行。这样,中共当局的意图便得逞了:他们就是要让人失去人被上帝所造而具有的荣耀,他们就是要让人成为“牛鬼蛇神”、成为“非人”。在此意义上,劳改营的生涯就是一个将人“异化”的过程,许多劳改营中的幸存者,长期无法摆脱漫长的梦魇、长期无法消除深入骨髓的恐惧。即便重新获得了自由,他们已经无法享受自由那甘甜的滋味了。
在此背景下,一个基督徒在劳改营中要持守信仰、捍卫人格尊严、维护上帝赋予人的基本的人性,需要付出比一般的囚徒大得多的代价。与绝大多数没有信仰的人、以及大部分在逼迫之下放弃信仰的人相比,俞崇恩、李慕圣和林淬峰这些基督徒,是经受住了试炼的精金,是落在大地里的麦子,是合乎上帝心意的器皿。如保罗所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罗马书》八章三十五至三十七节)在几乎不可能持守信仰的情况下,他们却成功地抵制了当局的洗脑,彰显了个人的信仰,成为主所喜悦的圣徒。
劳改营中有一套统治当局刻意制造的等级制度,在这套不成文的等级制度当中,基督徒处于最底层。俞崇恩在回忆录中说,在劳改营中,知识分子最受歧视,而基督徒知识分子更是“渣滓中的渣滓”。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人格的凌辱无所不在,死亡的阴影亦近在咫尺:“当时,我们知识分子的思想是被认为最臭的,所以分配我们多做一些臭的工作,以加速思想改造。有一个时期派我专门去埋葬死人。那些死人的遗物,一包一包堆在仓库里,每隔一段时间,这些包裹就要运到上海去,发还给家属。包裹都很小,没有几件好衣服。”19这种埋葬死人的工作既有羞辱之意,亦有恐吓的目的。任何人都不能不从死者的命运联想到自己的命运:“有一次分配我们班去把仓库里积存的小包裹运上小木船。我心里在想,这些家属没有收到这些包裹还好受一点;收到此包裹实在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一个活生生的人刚刚发配去改造,怎么就剩下这几件衣服回来了呢?当我看到那一次有几百个包裹运出去时,想到要是我的老母、妻女收到我的包裹,会怎么样呢!”20 那样的时刻,是人最软弱的时刻,也是人最容易放弃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