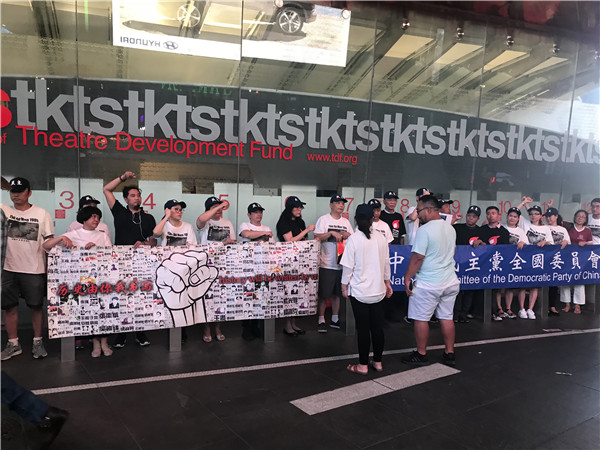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周素子更多文章请看周素子专栏
在五○年代初,我還只十多歲的時候,即知道夏與參其人,往後的數十年歲月中,由於我的生活變遷較大,“腳跟無線如蓬轉”,在杭州的時日不多,而夏與參雖則始終在浙江美術學院,見面的機會卻甚少。說起來我的家庭與浙江美院(其前身為國立杭州藝專)的淵源頗深:首是陳朗早先就讀於該校﹔次是我哥昌穀、昌米就讀於該院,畢業後任教於該院﹔再次是二幼畢業於中央美術學院後受聘任教於該院。半個世紀以來我結識浙江美院師生幾代人,與夏與參雖相同身為右派,可甚緣慳,與他只見過兩次面。
一九五二年我在杭州師範學校讀書,前在溫嶺初級簡師時的老師王伯敏當時在溫州師範學校任教,正活動商調到杭州國立藝專任教。王伯敏畢業於上海美專,後期專攻中國繪畫史。其年冬,他到杭州謀事,約我於一個傍晚到孤山訪夏與參。夏與參從杭州國立藝專畢業,在中共建國以前,他曾是當時學校學生運動的中堅分子,他思想進步,工作積極,據陳朗說,他還長於事務與管理才能,如籌款、舉辦義賣、救濟貧窮學生等。畢業時正逢中共接管該校,他被留校協助接管,且任教務、人事方面工作,有些實權。王伯敏想調入美院工作,故找他幫忙。夏與參當時住在孤山僻靜處一所藝專宿舍內,我們穿花度柳,曲徑通幽地找到他的住處,然“雨打梨花深閉門”,他不在家!我們在門口佇望了片刻,王伯敏甚為惋惜,他當時從溫州來杭,得經幾天舟車勞頓,何況謀事心切!這一次我沒能見夏與參,一直等到彼此成為右派,“生入玉門關”,得“落實”、恢復工作,之間三十多年的漫長動蕩歲月後,才在美院李家楨老師家第一次與他見面。 (博讯 boxun.com)
大約在一九八五年秋吧,李家楨請夏與參吃飯,在李家楨南山路美院教師宿舍中,因我為李家常客,故也被邀。其日,由李家楨的女兒李其容掌勺。原來李家父女二人,各有其友好。如逢女兒李其容宴客,在她相與的一班朋友中,我常為座上客。記得一九七九年冬其容宴請朋友,從中我得而結識了廈門才子王翼奇,後與他交往甚深(他後來任浙江古籍出版社副主編和副社長)。今則父親李家楨宴客,我也為座上客。在他家兩代人中,我的年齡居中,可謂兩無隔閡。那天見到夏與參,無絲毫生疏感。夏與參原名代育,字與參,以字行,四川人,鄉音濃重,個子甚矮小,小小的方臉盤,小小的手腳,穿著整齊、清潔。那天三人對飲,隨意而談,就談到浙江美院的極左思潮,遷校分水縣,扎根農村時的荒誕、勞民傷財、戕害知識份子諸況﹔喟感歲月流逝,舊友星散,多人亡故﹔談到美院歷次運動的極左表現,雕塑教授蕭傳玖因不堪屈辱而上弔身亡﹔王流秋的逃亡被捕﹔造反派頭目張永生在“四人幫”倒臺後病死獄中,以及某些人賣友求榮、鑽營、無恥,各派之間的毆鬥﹔更評論畫壇流派,新事、舊事……正是往事如煙!不覺夜深樽空,三人均微醺了。
夏與參當時已六十多歲,然尚獨身,似也無意成家。時正在勤奮習畫,並想另闢蹊徑,感情甚有寄托。據陳朗說,夏與參在求學時期曾致力於白描工筆人物,曾見其臨摹過唐周昉《揮扇仕女圖》等。惜甚少見其作品傳世。李家楨十分贊揚夏與參的潔身自好,生活謹嚴,說他在最艱辛的日子裡,也未曾見其有過生活上的拮据、狼狽。“文革”期間,浙江美院對所有“牛鬼蛇神”(包括地、富、反、壞、右以外的新、老階級異己分子、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每人每月只發給九元人民幣為生活費,例如我哥周昌穀,當時家有老母、妻子連他共三人,每月只發給二十七元人民幣。別人都不夠用,苦不堪言,而右派分子夏與參同樣的只這麼一點收入,但他節衣縮食,安排得當,除奉養(寄錢)在四川的老母使勿致凍餓外,居然還借錢給別的患難朋友,為人解急。
在李家楨家識荊以後,由於彼此忙於工作,未獲機會再與夏會參謀面。次年,也即一九八六年春,偶然的又有一次與他相見,地點為杭城吳山茗香樓。那天我陪老母登山賞花。我的老母生平最喜愛觀劇、賞花,四季中不論桃花、荷花、桂花、梅花,只要逢開放之時,必思外出賞花。比如孤山之梅,常盛開於風雪交加之時,老母則必穿上厚棉襖,纏上圍巾,作踏雪尋梅之舉。老母雖無書本知識,但對梅的花、蕊、萼、色、面,無不精賞,恐“梅王閣”主人高絡園也無此精到!平時在我們自己陋室閣樓屋頂陽臺上,老母即蒔花有五十餘盆,精心培植,護理,樂此不疲。
杭州城夾於錢塘江、西湖間,故東西窄,南北長,俗稱“腰鼓城”,吳山橫亙城中,將杭城分為南半、北半,更具形勝。吳山西連雲居山、桃花山,隔萬松嶺為南宋故都皇宮所在鳳凰山。吳山南麓一帶則為宋室皇族貴冑的別業遺址,遍山摩崖石刻,有宋米南宮“第一山”、蘇東坡“感化岩”並元麻曷刺密宗佛龕等勝跡。吳山之頂建有“江湖匯觀亭”。吳山上有若干棵宋樟,被榮冠全市古樹“一號”、“二號”……。吳山在城內,近在咫尺,山路平坦,為我母常臨之所。我母平日甚為節儉,凡蘿蔔頭、菜邊皮皆鹽漬作飯菜,但外出則喜嚐美食,不需多樣,但求精美。就在此繁花似錦的春日,我陪老母於吳山茗香樓進餐。進門,只見南邊明窗下若干人圍圓桌大啖高論,認得是美院黃裳等一干人。又見西窗下一人悠然獨酌,細辨乃夏與參也。我們就近入席相敘。夏與參說,該日美院部分教師聯袂郊遊寫生聚餐,他之所以獨酌,是因為大啖既費資又嘈雜,不如獨吃經濟實惠,落得清靜。我母甚贊賞他會過日子。
歸後,我將夏與參茗香樓獨酌之舉,說與我哥周昌米聽。我哥即談起夏與參斷橋相親軼聞一則:某年某日,有冰人為夏與參作伐,相約某女與他於白堤斷橋(即傳說許仙與白娘子初次會情處)相見。暮色蒼茫,兩人按時先後而至,各坐於斷橋石欄上。夏不與女者打招呼,也不寒暄,更不看女者,只看西湖。良久,以濃重的四川普通話作開場白:“我,夏與參,四十二歲,男,漢族……”道白完畢,回頭看女者反應,不料並無人影,那女人早已不知去向……。
這軼聞可能有“演義”成份,後來我續聽到有詳、略多種“版本”。大家之所以樂於傳述此一軼事,想來一則對他婚事的關切,再則對他特立獨行性格的激賞。我還曾聽陳朗的友人金尚義談起夏與參,除說他平時辦事的一絲不苟外,還說凡是舊友或與他有什麽瓜葛的人,從遠地而來訪求他,談事以後他總少不了一句鄭重申明:“宿食自理,恕不招待,我是六親不認的!”金君學著用四川鄉音說此話,甚肖。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