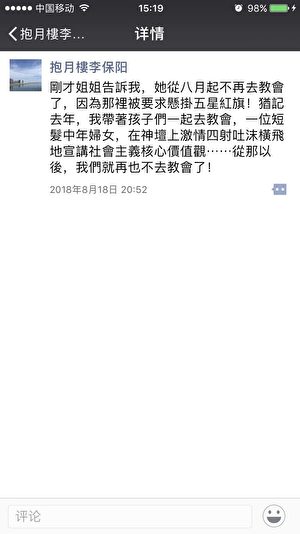林丹丹转至清莲居
“郭氏推特革命”的主体,其实就是近十年来出没在中国境内外社交媒体上的“网络革命党”,如水无定形。其中大多数成员都以“马甲”出现。最初形成于“零八宪章”签署时期,历经艾未未维权,在2011年“中国茉莉花革命”期间后备受打击,陷入凋零状态。
随着每年一半以上的应届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网络革命党”的人数越来越庞大。既然大都是失业、半失业青年(于建嵘称之为“底层知识青年”),让他们产生强烈社会仇恨的温床,当然是中国现阶段严重的社会不公。2015年7月,我曾在《革命的一只鞋已经落地》一文里,指出这些“网络革命党”从未消失,正处在“寻找领袖“的阶段。他们在“郭氏推特革命”中的表现,我一点都不意外,因为过去数年中,我曾经在多篇文章中分析过,这一切缘于中国现阶段严重的社会不公,以及对未来丧失希望。
第一重社会不公:源自教育资源不均的机会不平等
中国现阶段严重的社会不公,不仅体现在资源的占有、财富的分配,还体现在机会极不均等。对于出身于农村的中国青年来说,首先面临的就是教育的不平等,即城乡之间教育资源的不平等,如在农村地区实行了十多年的“撤点并校”,导致农村孩子上学极为困难,农村青年上大学的人、尤其是能够上重点大学的人明显少于城市。
据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郭书君在《我国农村高等教育发展状况的实证分析》一文中指出:1999年到2003年农村适龄人口高等教育入学率从1.4%增长到2.7%,城市适龄人口高等教育入学率从7.7%增长到26.5%。虽然都在增长,但城乡比值由1999年的5.5倍上升到2003年的9.8倍,差距逐步拉大。南开大学自2001年以来的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农村新生比例为30%,2007年这一数据为25%,2008年为24%,下降趋势明显。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北电力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近几年的统计则显示,农村新生比例最高时也不超过1/3。
这种不平等源于相关制度设计的不公平。中国各大中城市约有700所左右的重点中学,相比于普通高中,这些学校拥有更多的教育资源,比如较多的教育投资,因而能拥有更好的教师,更加豪华的教育设施。这些学校宣称其目标是培养最聪明优秀的学生,但一些学生借助家长的权势与金钱力量,利用高中可以推荐优秀生免考而直接进入名校。中国的精英大学常常与中学名校达成协议,大量录取他们的优秀毕业生。2010年,具备这一协议资格的近90所大学机构通过这一途径录取的学生占招生名额的30%以上;上海复旦大学这一比例则近60%。不能否认这些学校录取的不少学生确实优秀,但其中不乏有学生家长通过贿赂学校的方式从而使孩子获取录取资格。2015年,中国人民大学原招生就业处处长蔡荣生被审查时承认,在2005年至2013年间通过兜售大学录取名额共受贿2330万元(按汇价折合,约为327万美元)。
与其他国家在自由竞争之下自然形成的名校不同,中国的重点学校基本是在计划经济时代里,为了国家发展经济或者特定阶层的利益,通过行政权力人为地集中教育资源形成的“贵族学校”。这种优势一直延续到时现在,被舆论讥讽为“用全体人民的钱办少数人的学校”。
这种教育资源向少数人倾斜的制度设计,注定了农村青年(包括城市普通平民子弟)输在人生起跑线上。
2015年,中国政府加大了重点中学的招生难度,通过非高考途径(即高中以优秀生名义推荐直接上大学)获得录取资格的份额上限为5%,其余的学生只有当学生参加了高考之后才可获得录取资格。但在中国社会阶层固化、财富占有格局早成定局的状态下,这种矫正无异于杯水车薪。
第二重社会不公:社会上升通道严重梗阻
在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困窘中,大学毕业生求职的竞争变成了家世与背景的竞争,而不是能力的竞争。底层出身、尤其是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往往陷入一职难求的困境。
早在2005年,北京大学教师文东茅就写过一篇调查报告,名为《家庭背景对我国高等教育机会及毕业生就业的影响》。该文以全国范围招生的高校毕业生调查为基础,以父亲的职业地位和受教育程度作为衡量家庭背景的指标,其中专列一节分析“家庭背景对毕业生就业的影响”,指出父亲的职业状况决定子女的就业机会,其他如薪酬水平、提拔速度等,也都与父母社会地位直接相关。该调查表明,仅薪资一项,父亲的社会阶层越高,毕业生的平均起薪也越高,父亲为农民者比父亲为行政管理人员、经理人员的毕业生平均月收入分别少400元和300元。
这一调查揭示了中国阶层正在趋于固化这一残酷现实。几年之后,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中心的李宏彬等人做了一项同样的调查,接受调查的学生来自19所高校的6059名应届毕业生(重点高校10所,非重点高校9所)。调查采用问卷方式,内容涵盖了学生的个人基本信息、家庭背景,以及高考成绩、大学生活、毕业去向等。在接受调查的6059名应届毕业生中,有14%符合“父母中至少一人为政府官员(包括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这一划分标准,为所谓的“官二代”。研究成果表明,父母的政治资本对高校毕业生第一份工作的工资存在显著的积极影响,“官二代”大学毕业生的起薪高于“非官二代”。此外,从高考成绩这一智力衡量指标来看,“官二代”与非“官二代”并没有显著差别,因此“官二代”的工资溢价也不是自身的能力或智力因素导致的。比“非官二代”高出13%(约280元/月),这个工资溢价相当于两年教育的回报。
这种“资源的世代转移”现象,由于制度不公而加深,在21世纪以来短短十余年间,就造成中国社会上升管道严重梗阻、阶层固化的现象。
第三重社会不公:司法惩罚的不公
这种不公早就在司法过程中体现出来了,“我爸是李刚”这句话成了官二代耍特权的网络流行语。典出2010年河北保定一位市公安分局副局长儿子交通肇事之后,情急中冒出的一句话,意在要求警察看在他父亲的面子上不予惩罚,这位衙内说这句话并非无因,他从自身经历中得出的经验是:一般情况下,特权阶层的子女在违法犯罪之后,可以从轻处罚,甚至逃避法律惩罚。
特别让中国人不平的是,这种身份区别还反映在反腐败上面。自从习近平执政以来,反腐败力度起过以往历届总书记,王歧山也是历届中纪委书记当中最得力者,反腐成果超过中共前60年总和:省部级以上逾120人,军队中少将以上军衔者近60人。但奇怪的是,中国人虽然痛恨腐败,但对这张抢眼的反腐成绩单却鲜有叫好声,原因是这轮反腐的两条规则让人觉得不公平:一是反腐败为权力斗争服务,有选择性地反腐败,即以腐败为理由清除政治对手;二是反腐不触及红色家族,不少红二代与政治局常委家属积累了巨额财富,但这场反腐对他们基本不触动,落马高官基本上是平民子弟。不少贪官的故事披露后,前半截都是“苦孩子”奋斗向上的励志故事。
对这种服务于权力斗争的反腐败的不满,终于在2017年电视剧《人民的名义》放映后以荒诞形式爆发:社会同情度最高的剧中人物竟然是反角祁同伟。这位汉东省公安厅厅长,为往上爬不择手段,娶一位比自己大10岁的高官千金、为省委书记父亲送葬时声泪俱下地哭坟、官商勾结牟利、利用职权为亲属捞人赚钱开绿灯,为保安全不惜动用杀手杀人……,各种恶行昭彰,但因为祁同伟的标签是“家里穷得吃不饱饭”的“苦孩子”,属于中国那80%的下层(清华李强教授的最新调查数据:中国下层占人口比例为75.25%;再加上下层群体中与中产联接的过渡群体占中国总人口比例的4.4%)。从世纪之交开始,出身下层与准下层家庭的中国青年要晋身中产阶级已经很困难,遑论向上爬升。
一个上升管道严重梗阻的社会,不仅让人绝望,还会孕育强烈的社会仇恨。
以上这些,就是中国“网络革命党”产生的社会背景。在下篇文章中,我将分析中共如何通过持之以恒的意识形态教育与宣传,为自身培养了掘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