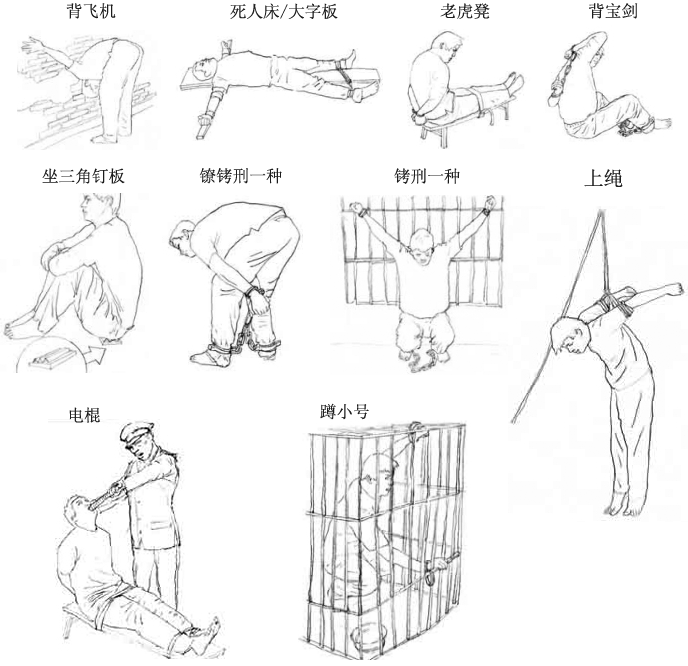赵宝儿转自:纽约时报中文网

香港——这家面馆周五晚上的生意很好,可容纳多人的餐桌边坐满了食客。在香港打工的外籍女佣埃妮·莱斯塔丽(Eni Lestari)注意到另一名女子旁边有个空位子,就赶紧把它占了下来。
莱斯塔丽说,那名女子突然站起身来,并声称不要挨着她坐。
该女子没有给出理由。但就在几小时前,香港政府下令让当地的37万外籍家庭佣工——大多是东南亚女性——做新冠病毒检测并接种疫苗。官员说,外佣是“高风险”感染人群,因为她们有“定期社交聚会”的习惯。
“他们不把我们当成也有社交生活的人看,”莱斯塔丽说,她20年前从印度尼西亚来到香港。“香港公众在新冠病毒流行期间的沮丧和愤怒,现在都发泄在外佣身上。”
莱斯塔丽没有在店里用餐,而是叫了外卖。
在世界各地,新冠病毒大流行已将外来打工者和其他低收入工人的困难处境暴露无遗,虽然这些人的劳动从底层支持着地方经济,但他们往往得不到承认或成为被剥削的对象。香港是世界上外籍家庭佣工最密集的地区之一,外佣约占工作人口的10%。
甚至在疫情之前,香港的外佣就已面临着广泛的歧视,她们的工作包括做饭、打扫卫生和照看人。她们只得到每周休息一天的保障,而且按法律要求必须住在雇主家里。外佣的最低工资是每月4630港币,但没有对她们工作时间的法律限制。虽然大多数在香港居住七年以上的外籍人有资格获得永久居留权,但外佣被排除在这项规定之外。
在疫情期间,政府官员和雇主们以公共卫生为由,将更多的限制强加于外佣。
据这些被委婉地称为“家务助理”的外佣描述,她们被禁止在休息日离开雇主家,名义上是为了防止感染。那些被允许离开的人说,她们外出时受到警察和路人的骚扰。政府多次指责外佣违反保持社交距离的规定,尽管香港的几次主要疫情都发生在包括其他外籍人士和富裕的当地人群体中。
香港官员发布的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强制接种疫苗的命令只针对外佣,不适用于每天都与外佣接触的雇主。
在公众强烈反对后,香港政府最终放软了态度。
“我们必须保护自己不受雇主的压力,也不受公众和政府的压力,”莱斯塔丽说,她是印尼移工工会(Association of Indonesian Migrant Workers)的创始人。“这些压力非常大。”
在两名外佣的新冠病毒变异株检测呈阳性后,政府在4月30日宣布了强制病毒检测和接种疫苗的要求。官员说,所有37万名外佣中,除了那些已经接种过疫苗的人,都必须做病毒检测。
外佣还需要在续签签证前接种疫苗。尽管全香港对接种疫苗的态度都很犹豫,但香港劳工局局长罗致光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外佣的情况与当地人的“不同”。他还说,如果她们不想接种疫苗,“可以选择不在香港工作。”
外籍工人谴责香港政府的这一要求是种族主义。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官员也表示反对,香港的外佣主要来自这两个国家。几天后,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取消了强制接种疫苗的要求,尽管她坚称,唯一的考虑是公共卫生。
但仍有强制病毒检测的要求——上周,林郑月娥下令进行第二轮检测,尽管第一轮检测只查出了三例阳性。
“这样做有什科学依据?”菲律宾籍外佣多洛丽丝·巴拉达蕾斯(Dolores Balladares)问道,她是倡导组织亚洲移居人士联盟(Asian Migrants Coordinating Body)的发言人。“难道他们还没有厌倦外佣是病毒携带者的想法吗?”
在许多外佣眼里,最新的公告是她们在疫情期间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最赤裸裸的例子。
官员已经加强了对外佣聚集场所的巡逻,并出动“流动广播”,提醒她们保持社交距离。
去年12月,一名立法会议员曾提议,禁止外佣在休息日外出。但她没有对外佣在工作日外出提任何限制,她们在一周中经常外出买东西、干其他杂活。
劳工局局长罗致光当时就拒绝了这一提议,他指出,家庭佣工中的感染率只有普通公众的一半。
已在香港工作了六年的菲律宾籍外佣马丽塞尔·杰米(Maricel Jaime)说,她对周日的无休止监督已有所预料(周日是大多数外佣的休息日)。在圣诞节那天,她和朋友们很小心地进行了一次小群聚会,并保持了社交距离。尽管如此,她说,每当她们临时靠得近点,比如把食物递给他人或从他人的包里取个东西时,警察都会赶过来训斥她们。
“警察一直围着我们转,总盯着我们。即使我们按照规定去做,警察仍骚扰我们,”杰米说。
警方也对当地人和外籍人士喜欢的餐厅和酒吧区进行监控。虽然当地人和其他外籍人士可以举行私家聚会,但外佣们别无选择,只能在公园、人行桥下等公共场所交往,因为她们没有属于自己的空间。
最近的一个周日,在中央商务区的一个街区可以看到许多聚在人行道上的外佣,十多名身穿米色制服的食物环境卫生署安全员几分钟就从旁边经过一次。他们或是提醒那些不吃东西或喝东西的外佣戴上口罩,或只是站在旁边看着。
一些外佣说,她们不觉得强制进行病毒检测的命令有问题。最近一个周二,一名外佣在检测点说,这是在香港工作的一个小代价,香港的工资比在印尼国内高得多。
但这种经济现实让那些感到受了不公平待遇的外佣很难保护自己。杰米说,她之所以选择来香港从事家政工作,是因为她在菲律宾当老师的工资无法养活她的父母。
“如果只有我自己的话,我宁愿回去,而不是在这种歧视下在香港工作,”她说。
能求助的法律很有限。12年前,香港颁布了反歧视法。但负责调查投诉的平等机会委员会从未代表投诉者在法庭上起诉过种族歧视案,香港大学研究少数族裔权益的法学教授普嘉·卡帕伊(Puja Kapai)说道。
尽管疫情引起了人们对外佣所处困境的关注,但卡帕伊说,她对政府是否会进行改革表示怀疑。香港经济已受到新冠病毒的重创,这让提高外佣的工资变得不太可能,而且香港居民中很少有人站出来为外佣说话。
“我认为香港政府没有多少采取任何不同措施的激励,”卡帕伊说。
尽管如此,一些外佣仍在努力引起变化。
杰米也是一个外佣工会的领导人,她说,每个周日,在遵守保持社交距离规定的同时,她都在试图让其他外佣知道她们的权利。
“因为新冠病毒,我害怕出门,”她说。“但我更担心这种歧视会越来越糟。”
中国民主党中共侵权民营金融观察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