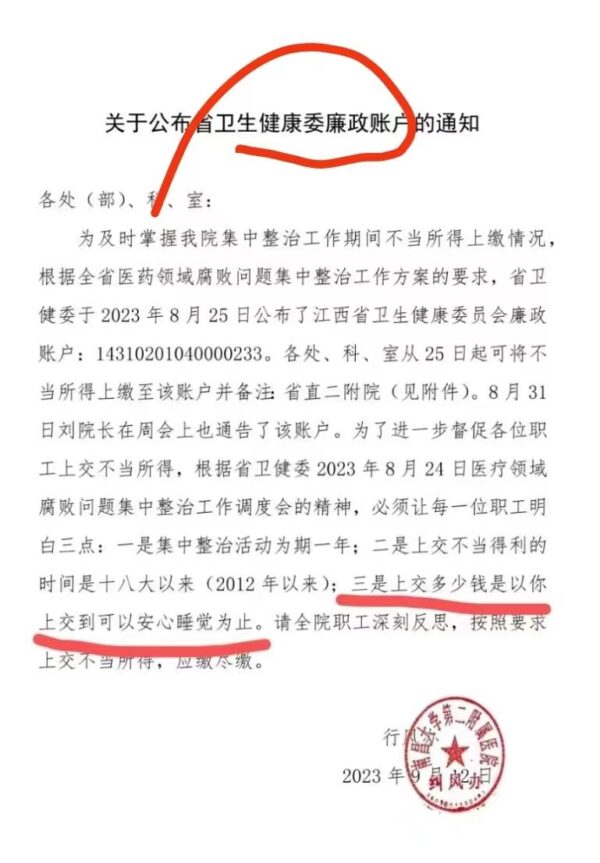焦玉柱转自美国之声

華盛頓 —
1992年,天安門事件三年後,來自英國倫敦的“香港監察”創辦人兼執行總監班內迪克特·羅杰斯(Benedict Rogers)第一次到中國教書,開啟了接下來30年為中國爭取人權的冒險與奮鬥。
在他將於十月出版的新書《中國節點:中共暴政內部及周邊三十年》(The China Nexus: Thirty Years In and Arou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Tyranny)中,羅杰斯詳述了從最初在中國學校和醫院教授英語、到香港主權移交後的前五年在港擔任記者,再到前往中國與緬甸、朝鮮邊境記錄難民逃離由北京支持的獨裁統治的經歷。
杰斯在書中特別聚焦維吾爾人、基督徒、法輪功學員、人權捍衛者、記者和異見分子以及香港人民的困境,對於強摘良心犯器官、種族滅絕等爭議性話題進行國際調查,採訪了80餘位一線親歷者、各國議員和學者,探討自由世界下一步應該做什麼。
2017年,羅杰斯被拒絕進入香港,今年初他成為自《香港國安法》頒佈以來,首位已知被香港特區保安局和香港國安警察警告、通緝的英國公民。目睹香港教區榮休主教陳日君樞機、蘋果日報創辦人黎智英等昔日師友一個個鋃鐺入獄,羅杰斯深感沈痛和心碎,但從未放棄希望。
羅杰斯5月31日接受美國之音專訪,他批評國際社會反抗中共侵蝕香港自由的措施過於遲緩和軟弱,他鼓勵香港僑民在海外積極進行政治遊說和推廣香港人的文化和身份。
羅杰斯指出,所有真正熱愛中國文化和中國人的人士,都應起身反對殘暴統治人民的共產黨政權。他認為,中國的人權迫害不會結束,除非中共領導層及其價值觀發生根本性變革,但是這在習近平的領導下幾乎不會發生。
記者:為什麼決定現在寫這本書,並起名為《中國節點》?
羅杰斯:首先,雖然有很多關於中國的書,但實際上很少有人將中國人權狀況的所有不同要素放在一本書中,很少有像這本書一樣既關注中國大陸的公民社會、律師、博主、吹哨人、持不同政見者,同時也關注香港、西藏、新疆、強摘器官和宗教迫害問題。我還決定寫一些章節,講述台灣受到的威脅,還有中國政權與跟中國接壤的兩個國家(緬甸和朝鮮)的共謀,這些地方正在發生嚴重的反人類罪和暴行,還有我專門研究的其他一些國家。這幅圖景逐漸出現在我的腦海中,我認為將所有這些不同的拼圖拼湊在一起會是非常獨特的。
我18歲時第一次去中國,在青島住了六個月教英語,我很喜歡這段經歷。我回去中國好幾次。。。除了人權狀況,我還想涵蓋個人的經歷以及對中國的思考。
寫這本書的另一個原因是,我真的想傳達一個我認為非常重要的信息,那就是我一點也不反華。正因為支持中國,我才關心人權狀況和中國共產黨政權對待人民的方式。我想傳達這樣一個信息:中國和中共之間是有區別的,我們都應支持中國,但我們都應反對中共。
至於為什麼選擇這個書名,通過這些年來在中國和周邊地區的經驗,我意識到中國是我個人生活的一個連接點(connecting point),而且當然還有在我工作的其他地方緬甸和朝鮮,中國是一個如此重要的因素。。。然後你看看今天的世界,中國是當今地緣政治中一個不可避免的因素,所以我把新書定名為“中國節點”(China nexus)。

記者:習近平5月30日會見了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任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發展一定會譜寫“新篇章”。這會是什麼樣的新篇章?
羅杰斯:可悲的是,我認為這是一個越來越黑暗的篇章。李家超體現了香港從亞洲最開放自由的社會之一淪為專制的“警察國家”的轉變。事實上,他自己的整個職業生涯都是作為一名警察,首先是任職警察35年,然後在政府工作。直到一年前他成為政務司司長之前,他在政府擔任的唯一職位是在保安局。他是梁振英政府的保安局副局長,然後是林鄭月娥政府的保安局局長。他熱烈支持林鄭月娥提出的一項命運多舛的引渡法案,然後是《香港國安法》熱切的執行者。
所有跡象都表明,李家超被選中是因為他將成為一個強硬的執行者。在安全領域之外,他沒有任何政府工作經驗,也沒有經濟政策、福利、教育或基礎設施方面的經驗。 他唯一知道的就是怎麼做警察、執法和使異見分子噤聲。我認為,李家超象徵著北京打算繼續執行並確實加強對香港自由和自治的破壞。
記者:回顧歷史,自1997或者2014年以來,有沒有哪些事情如果採取不同的做法,可能會保住香港的民主自由?
羅杰斯:我是香港末代港督彭定康 (Christopher Francis Patten) 的超級崇拜者。他是香港的支持者之一,即將出版擔任總督期間的日記。他在英國對香港最後五年的殖民統治中盡其所能為香港做正確的事。但我希望英國早點開始這一進程,並且在更早的階段做更多的工作,以試圖鞏固香港的自由並確保這些自由受到保護。
國際社會多年來眼看著香港的自由受到侵蝕,反應一直非常緩慢,直到過去幾年才改變。我們對2014年“雨傘運動”的反應非常不充分,如果我們採取了行動,實施制裁並使用其他工具,真正堅持讓北京遵守其在《中英聯合聲明》中的承諾,儘管事後很難知道這樣做是否會成功,但有可能不至於落到今天的局面,或者至少(香港)不會這樣迅速地淪陷。
但是相反地,英國和其他西方國家一直疏於應對,直到2019年的警察暴力和抗議爆發後才有所改變,然後真正到了國安法執行之後,民主社會才開始醒來,但是仍然做得遠遠不夠。比如英國過去一直沒有因為香港的自由被破壞而施加任何制裁,後來推出了很受歡迎的英國國民(海外)護照(BNO)簽證計劃。我稱讚英國政府此舉,但是這僅能幫助到試圖離開香港的人,對香港本土的情況沒有幫助。所以我認為,我們應該奉行一項政策,對北京表明,如果你破壞香港的自由,就會受到懲罰。
就香港的變化而言,我總體上是一個樂觀主義者,歷史表明獨裁統治不會千秋萬代。我相信這一天會到來,雖不知是否會在我的有生之年發生,但香港和中國終有一天會獲得自由。香港和中國的未來當然是緊密相連的,如果北京不改變,香港就不會發生變化。我希望北京會發生變化,會變得更好,這將為包括香港在內的所有中國人民帶來更多的自由。

記者:為什麼中共這麼害怕你留在香港?北京稱你為反華亂港分子,你怎麼定義自己?
羅杰斯: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我也經常這樣問自己。中國理應是超級大國之一,有望與美國持平,經濟實力甚至會在某些時候超過美國,它顯然也是世界上的軍事大國和主要的政治大國。但中國很擔心我的存在,這表明實際上這個國家並不像他們希望我們認為的那樣穩固,因為有安全感的人不會被像我這樣微不足道的人所威脅。
過去幾年來,不僅是今年3月我收到香港國安警察的來信,實際上還要追溯到2017年, 我在香港回歸週年之際寫了一篇關於香港局勢的文章。中國駐倫惇大使館不知怎麼發現了。在這篇文章發表之前,他們遊說了一位英國國會議員,試圖向我施壓,要求撤回我的文章。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來自北京的壓力。
2017年10月,我被拒絕進入香港。我本來打算私下拜訪老朋友和新朋友,了解香港的情況。 不幸的是,北京提前發現而且拒絕我入境。我可能是第一個有過這種經歷的西方人。從那時起,我經歷了各種試圖恐嚇我的方式。我收到了寄到家庭住址的匿名信,甚至我的母親也收到了匿名信。

我覺得很奇怪,一個本應自信的政府會作出如此極端、非理性的反應。我只能假設,中國真的害怕國際批評和國際壓力。事實上,我與我的同事在改變英國和其他政府的政策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我猜北京真的不喜歡這樣。但這說明了他們的不安全感。
我將自己定義為一個熱愛中國、熱愛香港的人,希望中國和香港都繁榮昌盛,在世界上佔據應有的位置。但要做到這一點,我認為中國需要並且值得擁有一個尊重人權、善待人民、不威脅鄰國、不試圖欺負其他國家的政府。
記者:關於新疆,你如何評價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巴切萊特(Michelle Bachelet)最近的新疆之行?
羅杰斯:我非常擔心這次訪問的性質和時間。當中國實施最嚴重的新冠病毒限制措施時,她去了新疆,這給予中國當局一個完美的藉口,拒絕她進入許多地方,甚至她最後一次新聞發佈會都是線上進行的。
我認為巴切萊特在最後一次新聞發佈會上的發言令人擔憂。她對中國政府讚不絕口,對中國的人權狀況輕描淡寫。她沒有提到(被公開的)新疆警察文件,這份文件幾乎是在她的訪問初始發佈的。她沒有提及維吾爾法庭(The Uyghur Tribunal)的判決,即發生在維吾爾人身上的是種族滅絕。她對香港的評論非同尋常,呼籲香港政府加強公民社會的空間,卻不承認公民社會在香港幾乎完全關閉。她沒有提到我認為是非常嚴酷的《香港國安法》。
所以我認為, 這是一個極度令人失望的訪問結論。巴切萊特似乎完全屈服於中共的宣傳、操縱和議程,粉飾人權狀況。這真的很可恥。
記者: 是什麼原因阻止巴切萊特說出真話和對中共採取大膽行動?
羅杰斯:這很難知道,我當然不想暗示有任何不道德的事情。我沒有這方面的證據,也不會這麼說。
巴切萊特似乎很重視這次訪問,幾乎不惜一切代價想要開展訪問並與中共對話,但真正的原因只有她自己知道。她在出訪之前甚至推遲發佈了她的辦公室關於新疆情況的報告,讓很多人非常擔心。如果她在來訪之前對新疆的情況輕描淡寫,然後訪問結束時發出強烈聲明,人們就可以理解為什麼她可能想要在訪問前小心行事。
但我不明白巴切萊特怎麼能在訪問結束時作出那樣的聲明。我真的不知道她的原因是什麼,除了她顯然希望與中共擁有良好的關係,以及不惜一切代價尋求對話和准入。
記者:你從最近洩漏的“新疆警察文件”獲得了什麼信息?國際社會應如何回應?
羅杰斯:新疆警察文件,集合了一系列文件、演講和照片,既說明了新疆局勢的規模和嚴重程度,也說明了這並不是由於某些官員行為不端或者由新疆當地官員驅動,而是來自(黨)中央和最高層,整個政府系統都對此負責。

記者:如何才能讓中共立即停止在新疆的暴行?
羅杰斯:當我為即將出版的這本書做研究時,我採訪了一些傑出的流亡維吾爾人,其中一位對我說,他們認為習近平之所以推行這個政策,是因為他每走一步,他要看國際社會的反應是什麼,然而幾乎沒有任何反應,他才敢繼續下一步,然後再走下一步。在每個階段,國際社會最初幾乎都視而不見,然後會在言辭上更加直率,採取一些措施,特別是通過美國。但是跟(習近平)所做之事的規模和嚴重性相比,國際反應仍然是不成比例地虛弱。
所以針對你的問題的答案是國際社會應該更加強大,反應要更加協調。我們需要協調一致的制裁。
不幸的是,問責是一項艱巨的挑戰,因為主要的司法和問責機構,比如國際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或國際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被中國的否決權和影響力所阻滯。但我認為應該認真考慮,是否可以由願意這樣做的國家建立某種特別的問責機制(ad hoc accountability mechanism)。
記者:天安門事件三年後,你到青島教英語,對於當時的中國和六四學運有什麼記憶?

羅杰斯:我在那裡交了很多朋友, 學生和我差不多大,或者比我小兩歲,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呆在一起。我也和一些老師交朋友。我去了很多人的家裡,收到很多邀請去學習做餃子。那時基本上是一段很有趣的、充實的時光。
雖然當時離天安門大屠殺很近,但還是有一種感覺,即在90年代和2000年的第一個十年,中國在某些方面開始走向開放。我當然並不天真,我知道存在限度,我知道中共過去、現在而且永遠會是壓制性的。但我確實感覺到並親眼目睹了某種程度的開放。
2000年代初期,我遇到了一群中國人權律師,當時他們還能工作,捍衛宗教團體和財產權、土地權、勞工權,當然也面臨一些紅線和監視。他們對我表示希望擁有這個空間,並且隨著時間的推移,活動空間會繼續擴大。當然,在習近平治下,所有這些律師都失蹤、入獄、被吊銷執照。
記者:如果中國政權不更替,上述這些人權迫害可能結束嗎?
羅杰斯:除非中共政權發生真正根本性的變化,即政權更迭,或者政權內部的人們的心態、心靈和精神發生改變,否則人權迫害不會停止。無論如何,只有在中共領導層以及領導層的價值觀和態度發生變化的情況下,(人權狀況)才會改變,但我認為在習近平領導下不會發生這種情況。
但是也許最近的封城在中國引起了一些不滿,還有經濟奇蹟的放緩,以及中國政府在國際社會中的聲譽下降,也許這些變數會共同積累,導致中共政權發生某種改變,但我們不知道變化何時會來臨。

記者:為改善中國人權的奮鬥旅程中,你有沒有感到絕望過,想達成的最終目標是什麼?
羅杰斯:我尤其記得2019年香港的抗議活動和警察暴行,還有2020年和2021年,《香港國安法》通過,他們逮捕了真正的英雄,如黎智英和黃之鋒等人。我有幸結識的香港朋友,可能再也無法相見和交談。
自國安法實施以來,一個明顯的變化是,之前我幾乎每天都與香港人接觸,現在幾乎是零接觸。我接觸過的大多數人要麼在監獄裡,要麼在流放中,或者變得很低調,我不想危及他們。這是具有挑戰性的,有時在情感上很艱難,但我從未失去希望,可能有時會感到心靈非常沈重,但繼續前進、發聲真的很重要。許多在監獄中的人所忍受的痛苦遠遠超過我,他們並未放棄或失去希望。如果他們至少能在精神上繼續前行,我當然也必須這樣做。
關於讓我繼續前進的原因,我的(天主教)信仰,這絕對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天主教香港教區榮休主教陳日君樞機(Cardinal Zen)是鼓舞我的人之一,他幾週前被捕真的令人心碎。我從他這樣的人身上尋求鼓舞和希望。歷史表明獨裁統治不會永遠持續下去。這些信念讓我繼續前進。我認為發光發亮和發出聲音,繼續提醒國際社會了解香港的現狀,真的很重要。
我的目標是看到一個自由、和平、繁榮的中國。幾年前有一個中國異見者寫了一本書,我不太記得書名,基本上說他的目標是建立一個基於愛的中國。我也認同這一目標,希望有一個自由、民主、和平的中國,維護人的尊嚴和人權的中國,可以成為世界其他地方的重要夥伴和朋友,而不是像今天這樣構成越來越大的威脅。
(美國之音進行一系列採訪,反映有關美國政策的負責任的討論和觀點。被採訪人所發表的評論並不代表美國之音的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