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湘辰转自VA
华盛顿 —
1931年开始到1945年结束的长达14年的日本侵华战争应该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黑暗的一页,作为当时中国的执政党的中国国民党为抗日战争付出了惨重的牺牲。然而,在中共党史的叙事中,中共才是中国人民抗日的领导者,始终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而实际上,中共一直保存实力,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甚至勾结日军。
无视国民党的巨大投入和惨重牺牲,中共坚称自己是“中流砥柱”
2021年最新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依然称中共是“全民族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对于中国国民党在抗日战中的巨大投入和惨重牺牲,新版的《简史》以一段话带过:“当时,国民党表现了一定的抗日积极性,国民党军队曾进行了平津、淞沪、忻口、徐州以及保卫武汉等战役,并取得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但是未能从根本上扭转战局”。
相反,《简史》以较为详细的笔墨描述了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参与的“唯二”战斗--“平型关大捷” 和“百团大战”。《简史》还这样突出这两次战斗的重要性。“平型关大捷是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主动对日作战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而“百团大战”给日军的“囚笼”政策以沉重打击,“在抗日局面比较低沉时振奋了全国人民的信心”。
事实上,“平型关大捷”只是国民党军队主导的太原会战中非常小的一部分。中共旗下的八路军只有林彪部不足一个师的军队参加作战。简史特别强调,“平型关大捷歼灭日军1000人”,但是绝口不提太原会战中光忻口战役就打死打伤日军约两万人,创造了华北歼灭日军人数的最高纪录的事实。
1940年8月开始的“百团大战” 是由中共八路军指挥员而非中共中央制定的战斗计划。中共中央在此之前只批准了小规模的包括23个团兵力的战斗。这一战斗后来在中共党内多年受到批判,认为它“在敌人面前过早暴露了我们(中的)的力量”。百团大战”的具体指挥员,八路军副司令员彭德怀后来在文革被清算时,进行“百团大战”是他“反对毛主席”的“罪状”之一。
史料显示,像太原会战那样的大会战,国民党在抗战期间共组织了22次(中日双方投入10万以上兵力)。另外,国民党还组织了1千117次大战役(投入兵力数万到十万人);3万8千931次万人以下的中小规模战斗。
与此同时,国民党军队伤亡341万多人,共有206名国军将领在抗战中捐躯。4300多名飞行员血洒长空,2468架战机被击落,海军舰艇损失殆尽。国民党75%的军力在战争中被消耗。
相比之下,根据中共自己的统计,敌后抗日武装共伤亡61万多人。中共方面在抗战中死亡的高级将领仅有左权1人。
中共对中国国民党在抗战中的地位与作用的最大限度的认可出现在2005年。2005年9月3日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在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讲话中说:“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这算是中共首次肯定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地位和作用。后来有一段时间,在中共官方的叙事中,出现过中国抗战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共同领导”的说法。不过,这样的有限承认,最近这两年也有了改变。
2019年,描述淞沪会战中国民党“八百壮士”死守上海苏州河畔四行仓库的电影《八佰》被撤档三次,原因据称是“过度美化国民党的抗战功绩”,只是展示了“历史碎片”。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抗战75周年的讲话中也不再提国民党在抗战中的奉献。“国民党”三个字全文只出现了一次,出现在“国民党军‘八百壮士’这组词中。到新版《简史》,国民党只是表现了“一定的抗日积极性。”
面对中国共产党史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的说法,《谁的新中国》一书的作者历史学家辛灏年在2005年在一场有关国共两党谁是抗战中流砥柱的公开演讲中曾提到这样一个问题:“我请问大家,淞沪会战中,中华民国投入的兵力是70万,日本投入的兵力是50万。两军对垒,120万军队在上海打起了一场决战。我请问,远离上海三、四千里以外的陕北红军,毛泽东领导的红军,一万三千杆枪、两万人马、三个县的资源,能够领导的了淞沪会战这样一场百万人的决战吗?”
在解释中共的“中流砥柱”作用时,中共党史的专家们通常会避开上述显而易见的力量对比的事实,转而强调:“中国共产党最早提出抗日主张并率先开展抗日斗争,是奋起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先锋”;“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并坚决维护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全民族团结抗战的政治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开辟的广大敌后战场和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是坚持抗战和夺取抗战胜利的决定性力量”等等。
那么,中国人民面临民族危亡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人到底怎么做的?
东北的抗日行动一开始并非是中共领导的
在中共的叙事中,“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的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最早开始。中共“率先提出了抗日主张,并率先开展了抗日斗争”,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了东北的抗战”。
2017年10月,中共的教育部将 “八年抗战”改成“14年抗战”,将抗战的起点,从1937年的“七七事变”,提前到了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外界认为,中共的此举就是为了凸显中共对东北抗日中的领导权,试图抢夺抗日战争的话语权。

中共的确在“九一八事变”后发表了五份反对日本侵略的文件。1932年,远在江西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也确实“对日宣战”,然而,这些并不能证明中共领导了东北的抗日行动。
东北的抗日行动最初是由东北抗日义勇军进行的。根据“杨靖宇(中共抗联领导人)烈士陵园暨南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的一篇题为“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兴起和发展”,“东北抗日义勇军”是“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各族人民、一部分东北军爱国官兵、山林队为基础自发组织起来的抗日武装力量”,“它的成分极其复杂,几乎包括了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
这篇文章承认当时的中共其实没有足够的力量来领导这支部队。文章说:“虽然中共满洲省委和地方党组织曾派出一批党员干部到一些抗日义勇军中开展工作,对义勇军开展抗日斗争起了积极作用,但力量弱小,不能左右抗日义勇军领导的决策,也无力解决义勇军内部成份复杂和思想复杂等问题。”
非但如此,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2013年的一篇文章指出,1932年中共中央“北方会议”“对东北中共的实际工作产生了极大的危害”。“北方会议”要求中共满洲省委在东北“实行土地革命,创造苏维埃政权,武装保卫苏联”。文章说,这样的政策因为排斥义勇军和山林队等错误,造成东北党组织的异常孤立,“使得党在义勇军中的工作归于失败”。这样的政策到1933年1月底才有所改变。
东北抗日义勇军后来发展到30万人,也有说50万人的,不过,1933年,由于遭到日军的围剿,义勇军损失巨大,几近瓦解。
1936年2月,中共满洲省委依照共产国际的指令,将所属部队以及义勇军残部联合起来组建了“东北抗日联军”。“东北抗日联军”最壮大的时候人数差不多3万人,规模不到义勇军时期的十分之一。抗联共有11个军,其中只有7个军隶属中共直接领导。
“新华每日通讯”2017年的一篇文章说,即便是中共领导的东北抗联也因为客观地理环境与中共中央的联系并非紧密。“地理上的距离加上当时并不发达的通信手段,使得东北抗联与党中央的联系极为不易”。文章还说,“由于同一时间上海党中央机关被叛徒严重破坏以及随后中央红军的长征,则让抗联与党中央的联络彻底中断,成了‘没娘的孩子’”。
1940年,东北抗日联军失去大部分的根据地和游击区,部队数量最后只剩不到2千人。这支队伍后来转向苏联求援,最后被编入苏联红军远东第88旅,也称“抗联教导旅”。1945年,这支队伍被苏联远东军解散。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号召推翻国民政府,“武装保卫苏联”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的六年间,中共到底做了什么?
中共中央的确在“九一八事变”的第三天,即1931年9月20日,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中共在宣言中谴责日军侵略,并号召工人、农民、学生、贫民、士兵全体起来推翻当时领导整个中国的国民政府。
同一天,中共中央代总书记王明还发表了“武装保卫苏联”的讲话。在这份题为《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中,中共中央给全党制定的“伟大历史任务”是:“武装保卫苏联,反对帝国主义的强盗战争”。
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这也不是中共第一次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号召“武装保卫苏联”。1929年,在苏联与中国因为“中国东方铁路”发生武装冲突时,共产国际要求中共“武装保卫苏联”,并组织大规模的反对国民党和拥护苏联的群众示威。中共对此作出了积极响应。中共创始人之一陈独秀由于反对“武装保卫苏联”被开除出党。
对早期的中共来说,中华民族并不像习近平所说的是他们要捍卫的对象,中国甚至都不是他们的祖国。中共成立的第二年就作出了如下明确的决议,“苏维埃俄罗斯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和农人的国家,是无产阶级的祖国,是劳苦群众的祖国……全世界的劳动阶级和劳苦群众应该尽力保护苏维埃俄罗斯”。
1931年11月7日,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中国在共产国际的要求下,在江西瑞金创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临时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坚持以暴力推翻领导抗战的国民政府为其基本宗旨。
1932年4月,中共中央发布对日战争宣言。这个宣言被中共党史当作中共领导抗日寻找的另一个证据。中共的宣传材料说,“这比国民党政府正式对日宣战要早9年”。但是,这份宣言不是号召民众首先抗日,而是先“组织民众抗日义勇军,夺取国民党军阀的武器”来武装自己,直接对日作战。
北京师范大学已故历史系教授王桧林2001年发表文章说,“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随后占领了大片中国领土,中国遇到了空前的危机,面临着民族生死存亡问题。但是,中国共产党按照共产国际和自己本党的决议提出的重要口号是‘武装保卫苏联’,自居于中华民族抗敌斗争之外”。
对中共来说,最有名的“抗日”行动无过于中央红军1934年的“长征”。毛泽东和朱德在1935年11月联名发表的《抗日救国宣言》中说,中共派出“红军主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历尽艰难困苦北上抗日”。关于这段经历,已有无数的资料显示,“长征”只不过是中共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的“战略大转移”, 更准确地说,“大逃亡”而已。
对于红军在中共军队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的几年间的行动,《中共如何壮大之谜》的作者谢幼田说,“中国共产党从来不是抗日的力量,不曾向日本军队放过一枪一弹,他们所做的,就是用红军打击国民政府,分散抗日的力量;或者利用民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抗日热情,与别有用心的政客配合,煽动立即抗战,破坏国民政府的战争准备和战略决策。”
相反,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因为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2年的“淞沪抗战”以及1933年的“长城抗战”而中止了对中共所在苏区的“围剿”行动。谢幼田说,中共的做法,“使得面对日本军队正面作战的国民政府的背后受到了一再的武装袭击。他们的作为,加重了中华民族的苦难和危机,而有利于日本的侵略。”
中共这种以暴力推翻国民政府为宗旨的革命策略到1935年8月1日中共发布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八一宣言》时也没有改变。《八一宣言》的策略是“反蒋抗日”。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共配合苏联的要求制定的
中共党史专家在谈到中共是抗日的“中流砥柱”时,都会强调中共首先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而是“全民族团结抗战的政治领导核心”。但是,中共专家们没有提到的是中共最初提出“统一战线”是源于共产国际和苏联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需要。
哈佛大学教授托尼·塞奇(Tony Saich)在自己的新书,《从反叛者到统治者,共产党百年》一书中说:“这最重要的战略转变再次来自莫斯科,来自1935年7月和8月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由于对德国和日本意图的忧虑日益加剧,共产国际七大呼吁建立反法西斯主义统一战线,包括所有成分、所有阶层和所有反法西斯的国家。”
中共宣传材料有时也会承认,“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新方针”,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经过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批准后,王明于1935年8月1日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了这份宣言,所以,这份宣言后来也被称为《八一宣言》。
《八一宣言》一方面“号召全中国人民动员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另一方面,又呼吁大家“冲破日寇蒋贼的万重压迫,勇敢地与苏维埃政府和东北各地抗日政府一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值得一提的是,彼时,中共中央以及毛泽东其实还辗转在长征的路上。用中共的话说,《八一宣言》的公布,“标志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战线基本形成”。
1935年11月28日,到达陕北的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发表《抗日救国宣言》,这被认为是中共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标志。不过,这个战线并没有包括蒋介石。宣言指出: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反蒋,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协定,而且愿意更进一步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
中共“反蒋抗日”的态度直到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之后,由于苏联的干预才有所改变,变成“联蒋抗日”。抗日统一战线能够真正形成,“西安事变”是重要的转折点,因为在西安事变后,蒋介石才接受了中共的条件,而这一切的转变都源于苏联的作用。
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和杨虎城劫持了蒋介石。中共一直强调,自己是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作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策略。但是,中国党史没有说的是,在得知蒋介石被扣押的最初,毛泽东和一些共产党人希望对蒋介石进行“公审”,“处死”蒋介石,而且,中共的态度遭到了斯大林和苏联的强烈反对。
《中共壮大之谜》一书的作者谢幼田说:“苏联认为只有中国的抗日战争才能够拖住日本,减轻日本对苏联东部的威胁;只有蒋介石才能领导中国和日本对抗,张学良不足以代替。”
另外,由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不同意,中共中央还放弃了与张学良和杨虎城达成的建立在苏联支持基础上的“西北国防政府”和西北大联合计划,下决心转过来同南京政府谈判。
哈佛大学的塞奇说,蒋介石最终接受中共的条件,答应与其一起建立统一战线是因为他相信苏联可以援助中国的抗战。苏联后来也确实为中国抗战提供了四年的援助。
塞奇说:“考虑到国民党军队在武力上的缺乏,来自苏联的支援非常关键。这也要求他(蒋介石)必须与中共达成某种政治上的安排。蒋介石因此不再抵制毛泽东的要求,允许中共保留自己的根据地,也接受对中共军队改编,将北方的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南方的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
1937年9月22日中共中央发表“共赴国难宣言”,包括为实现三民主义奋斗;取消苏维埃化运动,取消苏维埃政权以及红军的独立性等四项条件。23日,蒋介石发表实际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至此才算正式形成。
蒋介石成为国际社会承认的抗战中国统帅,中共也承认为其部下。濒临绝境的中共红军,因为苏联支援蒋介石抗日,从而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获得了难得的历史转机。
中共“七分发展、二分应对、一分抗日”
但是,被收编的中共并没有专注抗日,在“合法”的名义下,更为专注于自己的发展,最终夺取了政权,推翻了国民党。
偏居台湾一隅的蒋介石多年之后对此依然不能忘怀。1965年10月10日,蒋介石在《中华民国五十四年国庆纪念告全国军民同胞书》中说:“初不谓共匪毛贼狼子野心,竟玩弄其邪恶的‘两手’,方其投降宣言,墨汁未干,正当日军全面入侵之际,仍公然扬言,要‘七分发展,二分应对,一分抗日’”。

2015年9月2日,台湾总统马英九在台北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讲话时也提到这个方针,借此批评中共在纪念抗战时扭曲史实及抹杀国民政府对抗日战争的贡献。他还重申, 国民政府才是对日抗战领导中国的唯一政府,国军主导抗战是历史事实。
“七二一”方针的说法最初源于八路军第115师独立团团长杨成武手下一个脱离共产党的下层军官。这位叫李法卿的军官说,1937年9月,毛泽东对奔赴山西作战的杨成武指示:”中日之战是本党发展的绝好机会,我们决定的政策是百分之七十是发展自己,百分之二十为妥协,百分之十对日作战。” 李法卿还说,该指示是1937年8月,中共洛川会议秘密决定的原则。
关于这个“七二一”方针,历史学家们并没有从中共档案中找到任何证据。但是,这样的精神在中共领导人的回忆录的字里行间却有体现。
中共前领导人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对洛川会议有这样的记载:“他(毛泽东)警告会众不要为爱国主义所迷惑,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他主张八路军应该坚持游击战争,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避实就虚,绕道日军的后方去打游击。主要任务是扩充八路军的实力,并在敌人后方建立中共所领导的游击根据地。”
张国焘这样的说法与中共后来公开谈论的洛川会议的基本精神也很一致。中共的宣传材料说:“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和红军的特点,中共中央在会上确定了红军应执行的战略方针。毛泽东指出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并在有利条件下进行运动战,创立敌后抗日根据地,钳制与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保存与扩大红军。会议确定红军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使游击战争担负起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中共一直说自己是抗战的领导者和主力军,但在十四年抗战历史中,中共反复提到的只有“平型关大捷”和“百团大战”。这也可以从侧面证明,即便“七二一”的数据不完全准确,但是这样的精神至少是存在的。中共很少介入日本与国军的战斗。
共产国际驻延安特派员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写道:“八路军、新四军事实上从1941年开始就停止了对日作战,百团大战是最后一次对日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得到指令,一律不准对日进行作战行动,包括受到攻击便撤退。”
中国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奎松曾发文说,中共在统一战线成立的早期应该不太可能制定‘七二一’方针,但是,他承认,“1939年国共两党关系发生急剧改变后,到1940年,中共中央确实是“将军事发展放在了决定性的位置上,并且具体规划了‘在坚持游击战争的总任务下,扫除一切投降派和顽固派的进攻,将整个华北直至皖北、江南打成一片,化为民主第抗日根据地, 置于共产党进步势力管理之下,同时极大发展鄂中与鄂东’的大发展目标及其实际步骤”。
按照最新版《中共简史》,到1940年底,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部队发展到50万人(不包括东北抗日联军),还有大量地方武装和民兵,在华北、华中、华南创建了16块抗日民主根据地。
到抗战结束时,中共军队发展到约132万人,民兵发展到260余万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即解放区已有19块,面积达到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这是抗战初期中共的规模所无法比拟的。那个时候,中共只有不到5万人,正为自己的生存担忧。
中共对日本的真正攻击开始于1945年8月10日和11日。在距离日本投降还有几天的时间里,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连续发出七道命令,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迅即在华北、华中和华南地区展开攻势。在日军投降前一个星期,中共在上述地区迅速“收复县以上城市250座”。
中共此番表现令人不禁觉得其有“摘桃子”之嫌。历史学家辛灏年在其著作《谁是新中国》说,“摘了抗战胜利这个大桃子的,不是别人,恰恰是毛泽东和他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曾指骂蒋介石在抗战胜利之时,便立即从峨嵋山上赶下来“摘桃子”了,意即下山“抢夺”抗战的胜利果实。
毛泽东与日军勾结,出卖国民党
后来还有资料显示,中共非但没有认真抗战,而且还在抗战期间勾结日军,出卖国民党。
2015年12月,日本东京福祉大学国际交流中心主任、筑波大学名誉教授远藤誉出版了《毛泽东,与日军共谋的男人》一书。该书指出,抗战中毛泽东为削弱国民党军队的力量,把从国共合作中获得的国民党军事情报卖给日本;毛利用抗战壮大中共力量,为日后打败国民党军队做铺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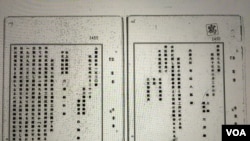
远藤誉的重要证据是日本侵华期间,外务省派驻上海的特务机构”岩井公馆”的主人岩井英一的回忆录《回想的上海》。根据岩井纪录,抗战期间毛泽东向上海和香港派遣中共特务袁殊、潘汉年等与日本特务机构”岩井公馆”和”梅机关”等接触,务求削弱抗日的国军并与日军签订停战协定。
远藤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她认为,勾结日军是毛泽东的个人行为和决定,然后由极少数间谍来实施的,这个行为并不是中共当时的集体决定,中共其他高层其实根本不知道这件事。
她还认为,中共建政后中共隐蔽战线最出色的特工潘汉年以及其他中共谍报人员的被捕应该与这段经历有关。1955年,潘汉年被秘密逮捕,后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越来越多的史料证明,逮捕潘汉年是由毛泽东亲自下达的命令。
共产国际驻延安特派员兼塔斯社记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1973年出版的《延安日记》也写到了毛泽东与日本军队勾结的情况。他写道:“我无意中看到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这份总部的报告完全清楚地证实了:毛等与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存着联系...... 电报无疑还表明与日军司令部联系的有关报告,是定期送到延安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