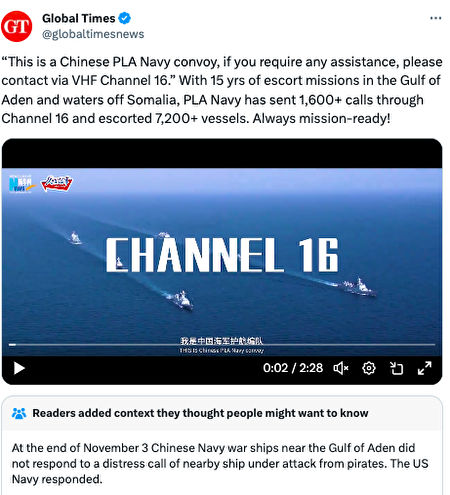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近来在反右派题材上的“夹边沟”叙事达到了新的深度,为世人睹目。但是在汗牛充栋的现代汉语文学作品中,描写“反右”的长篇小说十分少见,常见的多是零散的回忆和个人视角下的艰难叙事。作为长篇小说在宏大叙事上的缺席,固然是因为统治集团在反右问题上的遮蔽,同时也兀显出中国知识分子的的巨大软弱性和英雄人格的沦陷。正如谢有顺先生所说:“一九五七,这个巨大的时间烙印,正在成为中国人记忆链条上的复杂段落。尽管它是自由思想和知识分子命运在中国的重要转折点,也是二十世纪的中国第一次针对知识分子的大规模思想宵禁,标志着知识分子话语权利和批判品格的全面中断,事实告诉我们,记忆,居然成了这个时代每一个还有责任和良知的人,必须首先对付的精神难题。可不过是五十年时间,漠视和遗忘便已成了它最重要的敌人。”[1]
历史被割裂、中断,现场被不断毁坏,大部分当事人没有陈述的勇气和愿望,许多人都入已经融入市场经济丰盛的物质盛宴“欣然地活着”。“我活故我在”成了这个时代的人生主旋律,在这个时候青岛著名作家尤凤伟却把深刻、犀利的笔伸到了这段历史的最深处,企图对一九五七年的中国做一次X光透视。我们不能不对这种具有历史责任感的作家表示莫大的欣慰和尊重。进入新世纪以来,青岛作家尤风伟和刘海军分别写出了具有深刻历史反思题材的作品《中国:一九五七》和《束星北档案》,作为同乡我的欣慰中还充盈着骄傲。几次到网上检索,发现很难检索到原文,甚至不多的评论,也不容易找到和打开,有关本书的信息显然被冷处理了,就是在今年纪念反右50周年的海外文章中我也没有发现被谁提及,显然是在半明半暗地遮蔽中被清场、被遗忘,很少有人读到原著。可是,这是一部不可遗忘的小说,我以为她的存在、她的被知道、她的被阅读是我们思考这段历史重要的一环。
责任——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不是多不多,少不少的问题,也不是难易的问题,而是有无的问题,能不能最低限度在他们各自熟悉的领域担当的问题。不是要他们斗争,而是要他们面对真实和叙述过往。比如:对重大历史罪责进行分析清算的问题,从来不属于知识分子群体和和所有大众苦主,当局凭一纸《关于历史问题的若干决议》就摆平了所有重大历史问题,从此一切相关的评介都成为歪曲和反动,此时敢于针锋相对的勇士只是不多异数。但是作为作家有审视已经发生的历史的责任,有通过个人体验和事件对历史黑暗角落进行挖掘、重现和展示的责任,遗憾的是许多当事人就是大牌作家,可是他们的回忆和叙述缺乏足够的思想内涵,往往限于个人简单认知和个人遭遇的痛苦呻吟,而这些呻吟也是打了折的。我以为这些作家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早就有人指出:“尤凤伟选择了反右作为他的写作命题,可以想象,在当前的情势下,一定会遭遇巨大的困难,心灵和环境上的,因为他是在与遗忘、与日渐消失的记忆、与权力的强势话语、与历史悲剧、与人性的隐秘品性作斗争。”[2]的确如此,我在当地论坛中得知这样一个细节:春节拜年时一位友人和老尤就这篇小说简单交流几句,老尤说不得不考虑多活几年,希望能看到女儿出嫁,不然活到五、六十岁也就差不多了。这样的表白、这样的悲凉让我们看到作者宏大叙事后的焦虑。是啊,宏大叙事与渺小的个人命运的关系不能不是作者责任释放后的忧思。作者不是英雄,只是一个历史记忆的打捞者,一个思考着,焦虑着,并把若干既得利益置之度外的良知作家。
爱情——在极权压迫下,当人的本性丧失,生命尊严丧失,人沦为非人之后“五七人”活着还是死掉,为什么活着,为什么死掉的问题,显然是一个无法回避问题。作者通过不同人物的性格和命运给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值得关注的是为爱情活着,为什么为爱情活着,各自怎样为爱情活着是作者着墨最多的地方,也是最震撼人心的地方。书中主人翁周文祥和他的未婚妻冯俐在这个问题上的矛盾冲突是本书最悲壮的部分。
冯俐属于林昭式的铁女子,她固然热爱生命,追求爱情,但是她信仰的是真理,为了真理,她最终埋葬了自己的生命和爱情,义无返顾,没有犹豫、没有屈服。周文祥在身为“五七人”之后,信仰的是爱情,其实这是趋吉避凶这一人性弱点的必然迁移。不仅周文祥,其他人也是如此。作者详细描述了他在狱中对冯俐的揪心思念和对未来共同生活的憧憬。他的心灵生活就是思念冯俐,生存公式就是做梦,一次次的梦境:悬疑、恐惧、苦涩、盼望。为了这个最实际的目的,他可以在不丧失做人基本底线的前提下苟活着,他气急败坏的时候他也会擦枪走火,检举自己的伙伴。他知道自己与冯俐的距离,甚至在梦里出现冯俐的告戒:尔等“阉是必然趋势”,以此暗示自己业已属于阉类。可是,他不甘心自己的女人飞蛾捕火当英雄,出狱后他终于有机会当面劝说她,对于他的滔滔不绝,冯俐没有一个字的应答,她只是询问熟人的情况,并且嘱咐他“思想是气体、语言是液体、文字是固体”,没有文字留下来相应的历史就会成为空白,落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然后她煞有介事地将她特意为周文祥的到来而写的一份文字材料交给周文祥,结果那是数张无字的白纸。
当然,为真理和为爱情活着的结果有所不同,冯俐惨遭枪决,周文祥自由仅仅几个月再次因为文革的到来莫名其妙地入狱。
除了周文祥和冯俐的爱情悲剧,书中还写了张撰和王妃、俞峰华和小敏子的爱情悲剧,这几出爱情的悲剧都因为女主人命运的陡转而破灭,让我们看到的是一架制度性的悲剧加工机器。在劳改中的右派相当多都是绝望的人,此时他们不仅靠爱情情取暖,点燃未来,也靠爱情逃避真相和恐惧。可是他们往往无处可逃,哪怕他们的个人设计巧夺天工,天衣无缝。比如:张撰和王妃(枉费)的通讯方式设计,还不是被一位看好王妃姿色的首长横空出世的霸占所碾碎。
极权的真相——周文祥性格的复杂性(相对性),国家机器和极权制度不可理喻地单一野蛮性(绝对性),作者在二者的比照描写中对极权的真相层层剥离。书中有许多许多细节,撷其一二:
第一个撩动人心的细节是:右派们第一次割麦子,由于天热,大家不由自主地脱掉外衣,几乎每个人的背心上都印着某某大学、某某学院的字样,这是事实,但也很象是一次集体示威展示,管教自然要上纲批评一番,于是大家又不约而同地脱光背心,任凭麦芒针刺着……这个细节意味着知识分子无条件地臣服于“改造”。
第二个撩动人心的细节是:对周文祥梦的审判。周文祥习惯做梦,梦中常念念有词,自然有人仔细倾听,随后报告管教,幸亏报告者不够恶毒,梦中不过是几句简单的牢骚,也就草草过关。曾有人在梦中骂管教成了抗拒改造的证据被很很处罚。从“脱光”到“审梦”表现出对右派全面专政的深度和广度,即私人空间的全然沦陷,这其实就是极权的真相。近来的“彭水诗案”与其何其相似乃尔!
第三个撩动人心的细节是:在“马厩”里对“反改造”分子高云纯的批判会以及在"净身房"里对传抄屈原《渔父》的批判。对高的批判原于高的正直和嫉恶如仇的个人品格,也在于他的老婆是陈独秀的孙女,前者是致命的缺陷,是极权者必欲除之的眼钉,后者则是罗列罪状的道具。书中对传抄《渔父》的描写十分真实十分到位,文字狱一直是专制者不离手的一把断魂刀,它寒光闪闪足以让每一个健全的魂魄匍匐在地。《渔父》何罪?
当然全凭政府的肆意解释。他们的解释是——不管是海瑞还是屈原,都把党和人民比成封建帝王,抬出屈原无非是右派们以屈原自居,号召犯人抗拒改造,是一桩反革命政治事件。本来是老右们的丧志和自欺,结果成了进攻,这种被动语态与主动语态的错位,以及其调用的斗争哲学的辩证法实际上让整个历史错位,坠入深深地的黑暗。
书还有这样一个令人恐惧的细节:有一位即将刑满释放的管姓犯人突然越狱跑了。“老龚问:老管你为啥要跑呢?你不是只剩下两年刑期吗?……管勤说真他妈是大晴天叫雹子打破了头。那外调的公安人员问我在一九四九年那一年对我表弟说了些什么话。我说不记得了。公安人员说你表弟揭发了你,你必须如实交代。……陈涛问你在一九四九年多大年纪呢?管勤说十二岁。陈涛说十二岁还是个吃奶的孩子呢,未成年,法律是不追究的。管勤说表弟比我小两岁,要说我是个吃奶的孩子,那他还是个吃屎的孩子呢。他揭发的算数,我哪能没事呢?陈涛不吱声了。”
实际上红色历史表明,从革命的“儿童团”到反革命“小崽子”的煞有介事,都是极权逻辑判断选项上的选言肢。
正是这样严酷地、单一地、野蛮性制造的巨大恐惧,让周文祥们低下高傲的头颅,收敛起对真理的追求,祭起了“既来之,则安之”“识实务为俊杰”的万能旗子,用生存智慧自我保全兼自我缴械,随后接受洗脑、接受改造、“重新做人”也就顺理成章了。应该说这是绝大多数右派的心路历程,只要不刻意伤害别人,也就无可厚非。周文祥是软弱的,但是善良的,是正直的有道义底线的,也是无奈的和妥协的,除传统文化的阉人性格外,无疑这种性格的复杂性的形成是对应于专政机器残酷性的。
知识分子的真相——在中国担当真理和正义的始终是少数英雄,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经过“反右”和“文革”两次大围剿,知识分子的本相已经丧失,随后几十年的物质主义熏陶,尤其是89民主运动的铁血洗涤,保卫弱者,反抗权威的知识分子的本相几乎灭绝。那么,什么是知识分子的本相呢?
班达曾经给知识分子作过这样一个著名的定义:“知识分子是一小群才智出众、道德高超的哲学家——国王(philosopher-kings),他们构成人类的良心。”根据这一定义,真正的知识分子在任何时候受到真理和正义的感召时,都应敢于斥责腐败,保卫弱者,反抗权威。有时甘冒被烧死、放逐或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危险。(班达《知识分子之背叛》P43)这样的说法虽然不免有极端之嫌,但是,我以为,这才是知识分子应有的本色,也正是我们这个时代依然应该呼唤的一种特质。[4]林昭、遇洛克以及书中的冯俐虽然极其鲜见,但是这濒危的存在也算是暗夜中的曦光,好在近些年来我们看到了这种光芒的不断闪现。
《中国一九五七》的价值态势——《中国:一九五七》的诞生,是中国文化界的一件大事,它是知识分子话语权的一次胜出,在某种程度上洗刷了作家群体的耻辱;它也是文学样式和文本叙述的一次成功尝试;重要的是它使那段被遮盖的历史和被摧毁的人格得以重现,把80年代以来的“反思文学”推到新的高度,“从叙述的语调上来感受这本书,它没有痛定思痛的呼喊,没有悲愤、激越的张扬。平静,内敛,这种叙述品格追求的是真实的还原,仿佛一个亲历者在我们面前,对那段历史娓娓道来,虽然是在讲往事,却有恍惚其间的现场感。这样的叙述令人为之动容的地方,当然还是其间对人的关注。小说着力表现的是作为个体生命存在的人的价值是如何被摧毁的。小说表现的不再是一个知识分子蒙难事件,当然也不是国家社会的灾难事件,这是《中国一九五七》与许多同题材小说的区别。”[5]
在主人公的苦难历程中,我们看到的是人的自由丧失、人的基本信念失落后的惊人异化,主人翁如此写道“这里的我们早已没有‘人形’了,说的难听些都变成了一些狗,象狗一样听命于人,象狗一样摇尾乞怜,象狗一样不知羞耻,还有许许多多的象狗一样撕咬同类。我们已不是人,是‘非人’,反右运动的伟大之处正是将人变成‘非人’”[6]
此外,在历史现场的重现中,作者采取的的四声部立体交响式的结构,分别由:多种叙述交织的“京畿秋千架”(看守所、预审);日记体的“清水塘大事记”(改造、蜕变—人到非人的不自觉过程);第一人称自我流动辐射式的陈述“御花园遥祭”(人到非人的自觉过程);最具有特色的是第四部分“我乐岭人物志”。作者显然借用史志式的写法,对人名和场所类似《马桥词典》式的条目罗列,灵活多样地诠释了复杂的劳改现场(肉体和心灵的全面沦陷和重建记忆的挣扎),使中国的“古拉格群岛”初具规模。
这样一部具有丰富历史意义和文学价值的作品,在反右50周年的时候是应该被提及和重视的。这也是我不揣愚陋撰写这篇文章的初衷之一。
注:
1、谢有顺:《一九五七年的生与死》(尤凤伟《中国1957》小说跋一),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年1月第一版。
2、同上。
3、在所有监狱和劳改场所管教都代表政府,犯人的所有洗脑文本中管教和政府是互通的、一体的。
4、 班达《知识分子之背叛》P43页(郭梦霞:谁担此罪——读索尔仁尼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与尤凤伟《中国1957》)。
5、《南方日报》2001年6月15日。
6、《中国1957》P201页。
2007年12月上旬于青岛咫尺居
原载《民主中国》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