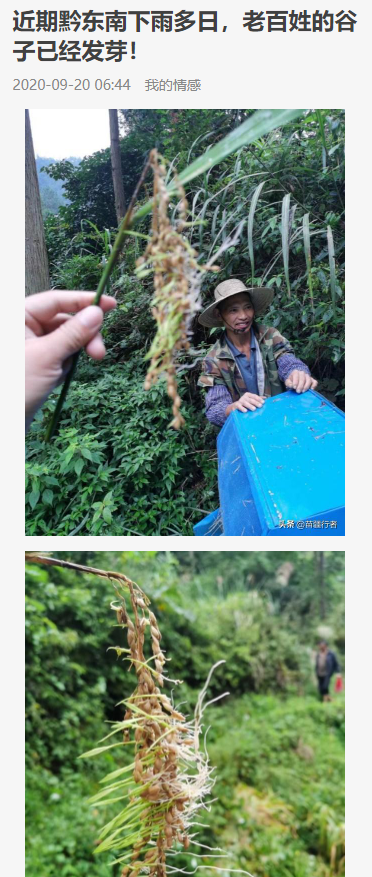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一九五一年我入讀杭州師範學校音樂科,校舍座落在西湖十景之一的“柳浪聞鶯”旁,原膺白路(現稱南山路)上,在清波門與鬧市口之間。當時校舍還未擴展,只有一座二層的“雄獅樓”為主體,教室全部集中於此,此外還有一些附帶建築,作為教師辦公及學生宿舍之用。飯廳極為簡陋,是個臨時性的大竹篷(現整個地區屬中國美術學院)。
(博讯 boxun.com)
杭州師範學校歷史悠久,與浙江第一中學齊名,是出名師、高徒的所在。在我入學時,教師陣容仍很可觀,如歷史老師張同光(後死於“文革”),音樂教育家顧西林(為音樂事業,終身未嫁,在“文革”中被迫害慘死),地理教育家勞天恩(右派份子,“文革”初期跳樓自殺),語文教師關非蒙(劃為右派,下放勞動,八○年代初“改正”後任杭州大學教授),政治教師潘紹光(共產黨員,後任第一中學校長,“文革”中被揪鬥,自殺身亡),語文教師宋清如(丈夫朱生豪, 翻譯《莎士比亞全集》最為優美、傳神者),畫家周天初(劉海粟老友,僥幸死於“文革”前)…….
我們這個音樂班,是杭州師範空前招收的第一班,原先有學生二十六名,後與蕭山湘湖師範合併增至三十多名學生。音樂專業老師即有俞紱堂、顧西林、黃永、丁蘭紉、沈同德等等,都屬一代有名望的音樂教育家。
音樂班的班主任為俞紱棠老師,浙江新昌人,從少年時代起,即在上海學習音樂,他的老師劉質平,是李叔同(弘一法師)學生豐子愷的學生,所以俞紱棠是李叔同的傳人。少年俞紱棠就曾為李叔同的歌詞譜曲、譜和聲而得過師公李叔同的表揚。
俞紱棠老師任教我們音樂科的音樂史論課、和聲學、對位法,並兼授鋼琴課、合唱課。那時已四十多歲,非常注重儀表,西裝革履,衣冠楚楚。他性格內向,語氣和緩,任教我班三年,從未見嚴詞厲色。夫人杜念杭,為其少年時期音樂學校同學(她父親為國民黨要員杜某,還是我父親在四○年代抗戰時期在安徽時的上司,並未出走台灣,記得五○年代初,我曾隨父親到杭州鳳山門火葬場禮謁過他的骨灰盒)。時亦在杭州一所中學任音樂教師。她與俞老師已有四個孩子,全家都住在我校的教師宿舍裡。杜夫人與我們這班學生並不太熟,大約她一回家就忙於家務了。夫人衣著樸素,其貌不揚,她的音樂修養程度,我們也不得而知。
我在杭州師範音樂科畢業後,再考入福建師範大學藝術系(那時稱福建音專),繼續學習音樂,與中學時代的師友就逐漸閡隔了。特別於一九五七年反右鬥爭中我被劃為右派學生,更與老師們音訊不通。一直等到七○年代初期,我自西北南返,則陸續聽到中學時代好些師友的悲慘遭遇,如七十多歲的顧西林老師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仍在關押隔離和臥病中,頭髮被剃成陰陽頭,受盡凌辱。我曾約會沈培堂同學去看她,結果不得相見。
至於班主任俞紱棠老師,先被打成“胡風份子”,一九五七年又被打成右派份子,處分甚重,開除公職,押送寧波鹽場勞動。曬鹽是很苦的活,讓一個音樂家去幹,而且一幹就是七年,真不堪設想!他終因繁重的勞動,艱苦的物質生活,與殘酷的政治壓力而導致精神失常,由親屬保釋回新昌老家養病、務農。夫人杜念杭還帶著四個孩子,仍掙扎在杭城教育界,她是如何承受杜家與俞家的雙重政治壓力,就不得而知了。這一切我只是聽聞。直到廿多年以後的八○年代初,我才又在杭城見到了俞老師,他苟活到落實右派政策的“改正”,但已到了退休年齡,浙江省音樂家協會聘他任《浙江音樂》編輯,並撰寫部分浙江音樂史。此時俞老師年已近七十,垂垂老矣,體態龍鍾,無復當年神采,本來不善言談,劫後餘生,變得更為沉默了。但他摯愛學生的心,仍然不變。
當年杭州師範音樂科的同學,為慶幸俞老師的健在,以俞老師為核心,召集分散在全國各地的同學們,在前後十年內,直到俞老師於一九九二年去世止,我們共聚會了四次。同學們遠從福建、湖南,近從寧波、金華、建德、湖州等處準時來杭,每次聚會都組織周密,佔二三天的時間,安排有序。當年的青年學子,此時也都屬五十多歲的人了,有的已有孩子的孩子了,但在老師面前,我們還是孩子。每次拍照留念,俞老師、杜夫人都會說“男孩子到這邊”,“女孩子去那邊”,多少的人生磨難,在這“孩子”的稱呼中,都洗刷了、純凈了。每次聚會都有杜念杭夫人參加,陪侍著俞老師,在這一對“白髮翁媼”身旁,我們都仿佛回到十六、七歲的少年無憂時代,所有的顛沛流離,各人程度不同的遭遇、苦難,都淡化了…….
末次聚會是在一九九一年,地址是母校新校址,結合顧西林先生的逝世紀念日,我們的同學們又從全國各地趕來。俞老師已經不能走路了,他自己為這次聚會特地買了一輛輪椅,由杜夫人推著前來。次年,我們這位少年時代的音樂教師即與世長逝 了,杜夫人一直體貼入微的照顧他,在風雨飄搖中伴隨他走完人生道路。在我們這三十多位學生中,有一個東陽人陳崇仁,他對老師的由衷熱愛,表現得最為突出。在校讀書時,陳崇仁是個極為平常的學生,俞老師並沒有給他過多的關注,但當俞老師罹難發配鹽場時,他卻一直關注老師,他在自己微薄的工資中節省下一些錢,不時購買食品為老師寄去。他怕老師在繁重的體力勞動中淡忘終身愛好的音樂,從而失去精神寄托,時時向老師提出一些音樂理論問題,向老師請教,老師在困境中仍對他作書面教導。在俞老師因病返新昌老家時,他專程前往看望。只有烏鴉的反哺精神能與他相比!當杜夫人把這段情節講給同學們聆聽時,大家都哭了。
我們的每次同學會,都由林光璇執筆、編纂,都留有詳細的記錄,其中有關陳崇仁的事跡紀錄特為詳盡。俞老師磨難一生,可安慰的是有一個安寧的晚年,與夫人為他支撐的可愛的家庭。老師的四個孩子,大兒子畢業於上海音樂學院,吹黑管,小女兒彈鋼琴,現在深圳工作。
來紐西蘭後,我收到同學呂英的一封信,她說《俞紱棠創作樂曲集》即將問世。我相信,這其中還傾注有杜念杭夫人的心血。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