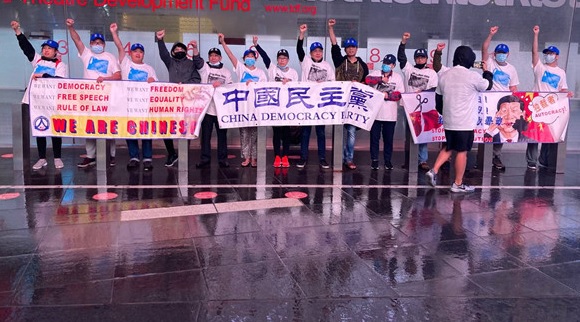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吳進是我哥哥周昌谷的同學。五○年代前後,他們都在杭州孤山之麓的杭州國立藝專(後稱華東美術學院浙江分院,現稱中國美術學院)學習繪畫,吳進比昌谷高一班,與吳明永同班,畢業後,分配到福州,在省美術家協會工作,反右前夕,任省美協主席。
(博讯 boxun.com)
我哥昌谷在美術學院求學五年之久,前後同學中有相當一批有成就的畫家、美術理論家,如現在北京的畫家林鍇、裘沙,史論家丁永道,在南京藝術學院的西畫教師陳積厚、茹民康,在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的美術編輯王仲清、張隆基、陳菊仙,在杭州任國畫教授的舒傳曦、劉國輝、孔仲起,西畫教授周詩成,雕塑家洪世清、徐永祥,海外潘其鎏等。尤其我哥的同班同學,畢業時共有十六位留校任教,為歷屆畢業留校任教最眾的一屆,其中如後任美院院長的肖峰(曾留學蘇聯彼得堡美術學院)、副院長宋宗元(本院國畫研究生),版畫張玉忠,油畫于長拱、馬玉如、銅版畫曹劍鋒,漆畫黃裳等等,都是當代畫界的中流砥柱,一代名家。
五○年代中期,從浙江到福州的火車未直通,要乘火車抵江山後換乘汽車,翻越仙霞嶺經浦城、建甌、古田,須經數日的舟車勞頓,野渡村店,方能抵達。那時我考取了福建音專,無人同行,有我兄昌谷的朋友程郁芬,為浦城人,時在建甌任小學教師,在中途建甌接待我。那時昌谷赴雲南寫生未回,由吳明永寫信給在福州的吳進,讓他在福州多方照看我的生活等等。第一次出遠門,汽車途經千山萬水,閩浙山區的木結構農宅建筑,其二樓均為一圈回廊,使建筑物呈磨菇形狀,宅旁老樹亭亭如蓋,宅後則峻嶺環峙,這一壯美獨特的景色,令我留下深刻印象。可惜那時並不知浦城為文化古城,留有明琴,有夢筆山,傳說為江淹夢筆生花之處,與琴樓等古建,失之交臂。抵建甌時已是月黑風冷夜十時左右了。
建甌是座古城,但見粉牆黛瓦,一律木結構住宅,鵝卵石舖路的小巷,迂回曲折,建陽江流經此城注入閩江,有大橋虹跨,使古城增色不少。郁芬過橋至車站迎我。她家住深巷木結構老宅中,數人的腳步聲更添老城幽巷的靜謐。她家給我燒了一大碗佐以香菇的面條,可惜香菇已經發霉,這該是深山中人藏以待客之物!
次日凌晨微熹中,我們又經過荒漠空曠的老橋,上車而別!我約於當日下午四時抵福州。滿目非故鄉之物,滿耳非故鄉之音,感覺似到了異邦他國。出乎意料的是,在車站碰到了我在杭州音樂學校的兩位老同學習聲樂的胡樹人(後為浙江師範學院聲樂教授)和習提琴的戴成基(後為浙江舟山師範學校教師),他鄉故知,歡喜無任。
在福州,我哥同學吳進算是親人了。我在學校同學中,亦很快交了一位朋友,她是閩侯馬尾港附近人,名叫林琴芳。她學習吹笛、彈琵琶。琴芳閩侯農家女,幼年時,父因負債,曾將她以抵債方式訂婚於某富裕農家,入學那年十八、九歲,梳短辮,鵝蛋臉,面色紅白鮮麗,明若海棠,眉清目朗,嘴唇稍顯寬厚,雖粗布衣衫,並不能掩蓋她混身勃發的青春。她從何而來的音樂細胞,並能考入老牌的音樂學校,不得而知。琴芳很用功,很有天賦,吹笛的姿態很美。
在校中我倆形影不離,一九五六年寒假,我未返杭,而是到琴芳家度歲的。鄉人待客,進門就是四個糖吞雞蛋,一天訪數家,就會積食不化。我最愛吃她家的蒸芋梗乾和紅薯乾。度假期間,我們曾到馬尾港觀七星塔。
至於吳進,他若不出公差,周末定來倉山看望我們,藝術系的美術科教師中還有兩位是吳進在浙江美院時的老同學謝意佳、林憶美夫婦,吳進每來我校,彼此如魚得水,歡暢無間。
一九五六年福州市舉行夏季音樂會,有我的鋼琴獨奏節目,演奏柴可夫斯基的《船歌》和王政聲教授創作以閩南民歌為主題的《漁歌》,彈奏所用的是省文聯鋼琴,因此我常到文聯練習,都與琴芳同去,吳進就接待我們,熱情親切,情同手足,我們叫他“吳進哥”。我們在他處,有吃有玩,無拘無束,甚感愉快。吳進哥經常誇獎說:“素子的才華,琴芳的聰明,都是舉世無雙的!”在閩江筏上,在鼓山、于山勝跡間,處處有我們的影子。吳進凡公差返榕,歡喜為我們帶回禮物。琴芳出身農家,無好衣,吳進還為她購買衣物。一九五七年暑假反右鬥爭前夕,我到北京看望陳朗先生,吳進哥還致信陳朗,讓陳朗細心看顧我,好好陪我玩。陳朗驚詫的說:“這還要吳進關照?!”
暑假返校後,反右鬥爭即席卷神州,我被劃為學生右派,為此牽連琴芳,也貼了她許多大字報,要她擦亮眼睛,看清身邊這隻披著羊皮的狼,要她與我劃清界線……。此時此刻,我真想能碰到吳進,得到他的慰解!但始終未見他的影子。有一天,路遇琴芳,她見四處無人,悄悄告訴我說:“吳進哥也被打成右派了!”
十七年以後,一九七四年,我流離在杭郊村店謀生。
一天,在韶華巷我哥昌谷寓舍,才又見到了吳進哥。他已年近五十歲了,頎長的身材更見消瘦,乾枯的面目更見蒼老,頭髮花白,他似乎仍甚樂觀,灑脫之情不改,絕口未提十七年磨難往事,只知道他在反右鬥爭後處分甚重,被送福建某山區勞動教養十五年之久,現仍孑然一身。從他口中知道琴芳的一些情況。他說琴芳畢業後,分配到南平二中任教。在後期的勞動生涯中略有鬆弛之隙時,他曾到南平看望琴芳。琴芳除任音樂課外還兼任女生指導,住女生宿舍內。按規定,男士不得入內,所以他與琴芳的幾次會面都在偏僻的小旅館內。在當時政治的白色恐怖如此險惡,身為教師、女生指導,竟能冒險在一個彈丸小城與一個政治犯約會,若感情不深,如何辦得到?!據說某個特殊假期,她還到吳進故鄉浙江義鳥鄉間看望過吳進,這令人想起雨果的小說情節!吳進從沒說起他倆的繾眷達到什麽程度。但他說,琴芳對他的感情是由同情而產生深情的。他從農場初回福州時,琴芳曾與其弟到福州看望過他。吳進嘆息說,如果不是反右鬥爭,琴芳肯定是他的夫人無疑。他說此生為琴芳也不想結婚了。但琴芳究竟有什麼阻礙而不能成為吳進夫人呢?在漫長的分離中,她的感情生活如何,均不得而知。吳進還說琴芳仍然常懷念我。根據吳進所提供的地址,我曾給琴芳寫過幾次信,均無回音。一九八五年以後,我調到《風景名勝》雜志社工作,有出差全國名山大川之便,我兩次到南平二中找過琴芳,事隔多年,竟沒有人知道她了,撲朔迷離,像《詩經》句“溯流順之,道阻且長,溯洄順之,宛在水中央”,“所謂伊人,在水一方”。在水之涘,在水之湄,琴芳在芷草、荇藻間,我尋覓不到她。
八○年代末,我堂哥昌米(現任中國美院教授),到福州開畫展,與吳進相遇,並到他家作客。吳進在六十多歲時與一個退休的越劇旦角演員結婚了。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