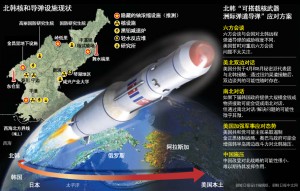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抗戰後期父親在東莞城外開一米店﹐名‘友興’ ﹐是和他的北大同學翟中森合伙的。位於中興路﹐即通往‘省渡頭’ 的河邊。‘省渡頭’ 指來往省城廣州的渡輪碼頭。這渡輪每天對開一班﹐人來人往﹐故中興路頗熱鬧。
‘省渡’上也很熱鬧﹐總是客滿。和珠江內河其他航線的渡輪一樣﹐它也是雙層客貨輪﹐上層載客﹐為二等艙﹐分上下鋪﹐臥席均以長條小木板隔開﹐每人約佔40公分寬。下層一半載貨﹐另一半為三等艙即統艙。它由小汽輪拖行﹐但駛離和停靠碼頭之際與汽輪并排﹐稱‘拍拖’ ﹐跟粵語意指談戀愛的詞相同﹐我覺得很有趣。而我們坐的二等艙上‘講古佬’(說書人) 的表演就更有趣。 (博讯 boxun.com)
這‘講古佬’ 屬江湖賣藝性質﹐全靠聽眾捧場給賞﹐所以使盡渾身解數﹐繪聲繪色﹐發揮得淋漓盡致。通常每程講一段﹐我聽過<水滸>首回高俅發跡那段﹐聽到端王(後為宋徽宗)是‘風流人物’ ﹐我問何為‘風流’﹐引起乘客哄笑。羊角哀﹑左伯桃和俞伯牙﹑鍾子期的故事﹐我也是在省渡上首次聽說﹐聽罷很受感動。此類‘講古’ ﹐多在從廣州開往東莞的船上﹐因是黃昏啟程﹐講畢已入夜﹐隨即各自休息。印象中未幾便駛至獅子洋﹐從艙壁小圓窗望去﹐夜色中一片煙波淼淼﹑浩瀚無涯的景象。朦朧入睡不久﹐聽見艙外高喊‘漳澎到了’﹐ 有時好奇地探頭一看﹐見一艘小艇靠在船舷﹐艇首汽燈發出微弱燈光﹐有人帶著什麼跨下小艇。片刻小艇撐開﹐省渡繼續旅程。這‘漳澎’ 跟隨後途經的厚街﹑道滘均屬東莞﹐厚街更與篁村相鄰﹐但我至今未曾踏足﹐亦從未在船上眺望過厚街和道滘﹐蓋均在夢中也。只記得往往一覺醒來﹐已近莞城﹐先望見金鼇洲古塔﹐號稱‘有舊無爛’ ﹐即塔身只會越來越舊卻不會損壞﹐和縣內另一古塔的‘有爛無舊’ 相反。不過﹐雖然該塔在省渡頭斜對面不遠﹐我也是迄今未到過。莞城掠影
省渡頭那時很簡陋﹐可謂又爛又舊。中興路大體為南北向﹐多兩層樓﹐房子還不太差。北面盡頭處接大西路﹐那是城外的主幹道﹐向西通往城內﹐為商業中心區所在。離路口數十米處﹐有一家門面較寬的百貨商店﹐那兒一位年輕店員長得挺帥﹐我和母親每次經過﹐他都會很恭敬地打招呼叫‘太太’ ﹐並送點東西給我。或是紅色的小鐵盒子﹐或是五顏六色的花紙﹐又或是香水瓶子﹐都屬於包裝材料﹐並不值錢﹐但其誠可感。我弄不清他是我們的遠親﹐抑或是我父親介紹他在那裡工作。
那百貨商店正當三叉路口﹐往裡走是菜市場。該路段舊稱賣麻街﹐路邊有許多攤檔﹐相當熱鬧。到了夏天晚上﹐週圍燈火輝煌﹐賣各種糖水的特別多。除奶白色的杏仁糊﹑紅色的紅荳沙﹑黑色的芝麻糊(謔稱劉﹑關﹑張﹐因粵劇中劉備臉白﹐關公為紅臉﹐張飛則臉黑) ﹐以及綠荳沙﹑杏仁茶之外﹐還有一種青麻茶﹐似為東莞特有。而且出售者會現場製作﹐他將若干青麻粒置於小厚瓦缸內﹐以短粗的木舂即時將其舂爛﹐再泡製出香滑的青麻茶﹐真是原汁原味﹐‘新鮮熱辣’。
此外還有若干提供梳頭服務的攤檔。檔主多為中年婦女﹐光顧者通常較年輕﹐一身鄉間女子裝束﹐往往是有備而來﹐也就是事先洗了頭﹐然後端坐於凳子上﹐臉朝外面的馬路。檔主立於其身後﹐為之塗上‘茶仔油’ ﹐再細心梳理。梳好後﹐女子的黑髮閃閃發亮﹐紅撲撲的臉上顯得容光煥發。我印象中﹐她們沒有一個不好看的。試想﹐在通衢大道上拋頭露面﹐跡近今日報名參加選美﹐必有幾分自信吧。少爺脾氣
大西路過了阮涌入口處﹐轉九十度向北﹐約50米外再轉九十度復向西﹐兩處轉彎的地方旁邊各有一茶樓﹐都是位於二樓﹐同屬莞城最高檔次。臨街的窗子玻璃色彩繽紛﹐煞是觸目。我十一舅幾次在那裡請我們一家‘飲茶’ 。他名應泰﹐時任鎮長﹐在黑白兩道都有面子。有一回他大排宴席﹐整層樓都包了﹐好像是為我母親祝壽。不知何故﹐我突然發起少爺脾氣﹐衝撞了他﹐具體細節已忘﹐總之是在大庭廣眾之下﹐把他弄得很難堪。母親再三哄我也無濟於事。最後我竟拂袖而起﹐衝了下樓。今日思之﹐羞愧莫及。
類似的撒野我非止一次﹐之前患傷寒於廣州住院時也發生過。那次是一位鄉鄰---曾在我家當女佣的‘阿嬸’﹐ 專程到醫院探我﹐同時跟我們道別。她剛獲悉抗戰時失散的兒子還在生﹐而且當了空軍飛行員。她準備啟程赴雲南母子團聚。我本應感謝她來探病﹐並為她的好運高興。可我莫名其妙地大發雷霆﹐堅決不讓她進我的病房。半個多世紀後回想此事﹐我真懷疑自己是否有潛在的心理變態﹐以致某個時刻會突然失控﹐做出極不理智的蠢事﹐既損人又不利己。麥屋豪宅
緬懷往昔﹐免不了或生羞愧﹐尤其是少不更事之時。但童年生活畢竟亦不乏若干樂事。我對彭屋大街的回憶﹐就和美味的燒鵝腿連在一起﹐也和母親娘家古老寬闊的祖屋---麥屋分不開。
彭屋大街是城內的主要街道﹐後名市橋街﹐跟城外的大西路相連﹐但比後者窄得多﹐而且是麻石鋪就的老式街道。可是這街上一家燒鵝店卻遠近馳名﹐似乎城外無可與倫比者。它正對著麥屋。每逢母親或六姨帶我到麥屋﹐探望住在這裡的十一舅和姨媽﹐定會買燒鵝腿給我吃﹔而十一舅母也一樣﹐常把對門的招牌佳肴作為款待小輩親戚的例行食品。本來我以‘擇食’(挑剔食物) 聞名﹐但對燒鵝腿並不抗拒。另有一種東莞土產‘臘鴨腎’ 我也樂於接受﹐那間店舖似乎也能買到。它的門面其實不大﹐比起麥屋簡直小得可憐。
就我所知﹐整個東莞城內麥屋算數得上的豪宅。後來我讀<紅樓夢>﹐覺得大觀園的花團錦簇難以想像﹐就把麥屋設想成微型的大觀園。據我一位表哥描述﹐其房舍大體可分為四部分﹕
一是主體﹐包括前三進和後面的書房﹑橫廳。‘進’ 與書房結構相似﹐均由正廳與東西廂房組成﹐正廳前天井兩邊各有廡廊小屋。二是東套屋﹐位於主體東邊﹐隔一露天甬道。其規模仿若一‘進’ 而稍大﹐且有門間。三是西套屋﹐位於書房後方﹐與橫廳隔一小天井。其面積較小﹐只有前後兩間﹐中有天井分隔開。四為附屬房舍﹐包括上有閣樓的舂米間(也有門通小巷) ﹑洗澡間﹑柴草房及面積頗大的穀倉。穀倉外有地塘。最後面是花園。相依為命
可能是祖輩安排﹐麥屋由麥樸農後嗣居住。故該豪宅雖房舍眾多﹐實際上十一舅一家居於其內時間最長。我母親和她的九個姐妹﹐按慣例均不能入住其中。
所以﹐儘管六姨﹑八姨當時都在莞城﹐卻自己租房子住。而我們每次到莞城﹐必然到她們合住的地方﹐同時探訪六姨的婆婆‘阿瑪’ 。她們婆媳倆幾十年來一直相依為命。
六姨名凌霄﹐小名長春。母親叫她‘阿春’ 。她是十姐妹中最聰明伶俐的一個﹐也是讀書最多的一個﹐亦是僅有擔任過公務員的一個。抗日戰爭之前﹐她一直在廣州市政府做事﹐晚年她曾對我說﹐最愜意的是在煙酒專賣局任職時﹐十分清閑﹐‘沒什麼事要做’ 。對我母親她很敬重﹐總是親切地稱之為‘多姊’ ﹔對我九伯父的人品學問讚不絕口﹐並且隨我們兄弟的稱呼叫他‘九伯爺’ ﹐而九伯父則回稱之為‘六姨’ ﹐其實他年長14歲。
她念念不忘九伯父伸出援手的一件事。那是40年代初﹐她受人之托﹐護送一位名叫容嫻的同鄉到粵北﹐與其丈夫團聚。容嫻之兄容庚﹑容肇祖昆仲均為著名文字學家﹐跟我父親相交幾十年﹐可謂通家之好。我們兄弟稱他倆為大﹑小‘容世伯’ ﹐叫容嫻‘容六姨’ ﹐稱其姊容七珸‘七姨媽’ 。後者學過助產士﹐粗通醫道﹐抗戰時曾跟我們同住篁村﹔前者卻居於廣州。雪中送炭
話說那次六姨護送容嫻﹐從廣州出發﹐所帶行李甚多。六姨雖出身富豪﹐為頗通文墨﹑出口成章的大家閨秀﹐卻是拿得起﹐放得下的女中豪俠。容嫻則生於清貧的書香門第﹐兩歲喪父﹐應變能力不強。故一路上全靠六姨照應。戰亂期間出門在外﹐其艱難一言難盡。好不容易兩人到達韶關﹐找了間小客棧投宿。略作安頓後﹐第一要事為洗澡﹐蓋連日趕路﹐身上早已邋遢不堪﹐滋味難受之極。不料該客棧竟無浴室﹐老闆表示歉難相助。六姨情急智生﹐即打電話給遷至當地的省政府﹐找我九伯父設法幫忙。接電話者為‘溱哥’ 梁繼溱﹐他是九伯父大女婿﹐時任廣東省政府機要科長﹐與六姨相熟。聽罷六姨訴說﹐馬上驅車趕來客棧﹐將她和容嫻接走﹐轉而入住一高級旅館。六姨她們遂得沐浴更衣﹐精神大振。而九伯父亦聞訊趕到慰問﹐口口聲聲‘六姨’﹐ 備極謙恭。旅館老闆則對之肅然起敬﹐頻呼‘秘書長﹐秘書長’ ﹐蓋九伯父乃省府主任秘書﹐省長李漢魂轄下要員也。
此事對六姨當屬刻骨銘心﹐故她80多歲時仍一再提起﹐對九伯父以及溱哥雪中送炭之舉感念不已。她口才一流﹐講得娓娓動聽﹐我屢聽不厭﹐並在腦海中想像九伯父當年的風采﹐為之心往神馳。搓‘炮仗’
然而﹐抗戰勝利後﹐一向為官清廉的九伯父力有不逮﹐再也不能澤被六姨了。年過四十﹑早已孀居的六姨﹐於戰時痛失愛鍾愛的幼子‘阿炳’﹐ 又無就業機會﹐靠出租少量土地﹐所得菲薄﹐生計困難。但她並無怨天尤人﹐而是勇敢面對。她與家姑‘阿瑪’ 居於莞城﹐容庚教授請她協助﹐做些古畫鑒識的輔助工作﹐阿瑪則於家中接外判手工活﹐如將光身的火柴枝插入一圓盤﹐以便加紅磷於頂端成火柴頭﹔又如將鞭砲(‘炮仗’) 砲身搓緊之類﹐後者東莞稱為搓‘樸’ ﹐與前者俱屬從業人員頗眾的家庭副業。
我們每次到六姨家﹐‘阿瑪’ 多是端坐於木製搓‘樸’機前幹活。該機為門狀結構﹐中間橫梁上懸一單擺形重木﹐呈圓弧狀﹐擺動方向與橫梁相垂直。其下固定一同為弧形的底座﹐與上懸之木擺相隔約七八公分。操作時﹐取一待搓緊的寬鬆炮仗身﹐將其置於弧形底座頂端﹐然後以手拉起木擺﹐待其過了底座頂端位置﹐即將木擺推下﹐炮仗身被擠壓於兩者之間﹐並隨木擺之運動而被推送至底座最低處﹐從而搓成緊密牢固的半成品﹐再加裝火藥及插入引線即可燃放。
一見到我們﹐‘阿瑪’ 會立刻放下手上的活﹐倒茶端糖果﹐熱情款待我們。我們也很自覺﹐即時接替她的工作﹐或搓‘叵’ ﹐或插火柴枝﹐反正這是小孩也能幹的活﹐也不耽誤一邊說話寒暄。
這時候﹐在裡間房子改作業的八姨也會聞聲出來﹐同我們閑聊一會。她名淑芳﹐小名‘阿珠’ ﹐不過這是我母親跟六姨對她的叫法。八姨丈姓馬﹐曾在湛江市任法官﹐抗戰勝利後不久去世。八姨回到莞城教小學﹐很受好評。她長期擔任五﹑六年級班主任﹐據說管教頑劣生相當得法﹐再怎麼搗蛋的‘百厭精(刺兒頭)’ ﹐到了她的班就變得服服貼貼。不知是否因她久為人師﹐對我們這些年輕的後輩嚴肅有餘﹐不像六姨使我們如沐春風。老實說﹐我從小就怕她。
她有個女兒﹐名湘﹐其實是十一舅母所生﹐由她收養。也許是八姨丈去世早之故﹐又或是八姨教導有方﹐湘表姐特別剛強自立﹐很有主見。她比我大姐小6歲﹐記得1948年我們暑假回鄉﹐大姐在東莞中學籃球場學自行車﹐她在後面扶持﹐一面以教練口吻﹐不斷說著﹕‘坐正’ ﹑‘把穩’ ﹑‘對了’ 等指導性語句。我在一旁見此情景﹐以為是她教大姐。不料50多年後﹐一次她經港返美﹐閑談中我提起此事﹐她竟說自己那時還不會騎車。她一向說話語音輕柔﹐和八姨截然相反﹔但當日卻顯得剛勁粗獷﹐以致我產生錯覺。二姐左傾
我姐姐和表姐們幾乎全比我年長得多﹐跟我最相近的二姐﹐也差不多比我大八年。
她跟大姐原來都在執信上學﹐但念高中時就轉到長風中學。執信是為紀念孫中山先生親密戰友朱執信而設﹐歷史悠久﹐國民黨當局很重視。該校離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很近﹐環境不錯﹐校園設備甚佳﹐其主樓是座宮殿式建築﹐紅牆綠瓦﹐頗有氣派。姨媽寄居於二表哥家中時﹐我多次往訪﹐印象中執信一派嚴謹莊重的書院氣氛﹐女生們都穿著整齊劃一的藍色校服裙﹐不苟言笑。據說﹐學生們一般家境都不錯﹐雖非培道﹑真光一類教會辦的貴族學校﹐但絕對屬於保守正規之列。於是﹐思想遠較大姐激進的二姐﹐讀完初中轉學便成必然之舉。
長風中學位於河南下渡村﹐與當時的嶺南大學為鄰。它是抗戰勝利後創辦的一所私立中學﹐是由一批西南聯大的畢業生為主建起來的。所謂西南聯大﹐全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是抗戰時期(1938-1946)北大﹑清華﹑南開三所大學聯合而成﹐名教授雲集。名師出高徒﹐畢業生中精英匯萃。所以長風師資強勁﹐校風尤佳﹐它的民主精神十分強烈﹐其艱苦辦學更是感人。
我曾跟二姐去過長風。只見學校的禮堂兼飯堂是個大竹棚﹐頂蓋葵葉﹐週圍一圈是葦蓆。校內一座樓也沒有﹐教室全是平房。生活用水靠井水﹐井深﹐打水頗吃力。學生多赤腳﹐無校服﹐男生課餘往往穿背心短褲﹐很隨便。但師生關係融洽﹐無分彼此﹐洋溢著輕鬆活潑的氣氛﹐與執信判然有別。而中共的地下組織‘民主青年聯合會’ 在此更甚為活躍﹐故該校有‘民主堡壘’ 之稱。國民黨當局自然對之很頭痛。
父親是國民黨員﹐儘管早已退出政界﹐但對中共有戒心。然而﹐二姐的左傾他沒有明顯反對。我自然還不懂政治﹐也不覺得她對家人的態度有什麼改變。按說﹐她在兄姐中跟我一起的時間最長﹐但感情並不特別深。她曾兩次救我脫險﹐一次是在化龍里村口旁的小溪﹐我從岸邊失足滑下﹐被湍急的水流沖走﹐幸虧她一手捉住我的胳膊﹐將我拉回岸邊﹔另一次是在莞城河邊碼頭上﹐我沿石階下水洗澡﹐走了幾級﹐不知石階已盡﹐一腳踏空﹐沒入水中﹐身子直往下墜。奇怪的是﹐那瞬間竟很清醒﹐也沒怎麼掙扎﹐只是想道﹕‘這回糟了﹐小命沒了﹗’就在此生死關頭﹐頭髮突然一緊﹐身子隨之上昇﹐眨眼間口鼻已出離水面﹐可以正常呼吸了。定睛一看﹐原來是二姐抓住我的頭髮﹐將我救起。但我當時及事後都並不特別感激她﹐兩次均在場的母親也沒有為此讚揚過她﹐甚至從來沒有當我的面將此事告訴家裡人或親友。大家閨秀
比較起來﹐大姐似乎更受母親鍾愛﹐而她又是個很會討人喜歡的女孩﹐長得很清秀﹐生性文靜﹐言辭得體而有書卷氣﹐頗見大家閨秀風范﹐英文學得特別好。她比我約大十二年﹐總是和氣地關心我﹐呵護我。
我永遠忘不了那年暑假﹐她在我跟母親的臥室﹐給我講大仲馬的<基度山恩仇記>﹐接連講了好幾個傍晚﹐我如飢似渴又如痴如醉地每天追著聽。最後講到基度山脫去紳士服﹐以水手裝現身於鄧格拉斯面前﹐自稱﹕‘我是愛德蒙。鄧蒂斯﹗’她提高了聲音﹐充滿了復仇的快意﹐我亦得到極大的滿足。此情此景﹐至今如在目前。
她看的<基度山恩仇記>是英文本﹐我們家也有一本﹐不過只是第一冊﹐即寫到鄧蒂斯脫逃得寶報恩為止。封面是艘老式西方大帆船﹐裡面有幾幅版畫插圖﹐其中一幅畫的是懸崖邊上有兩個人﹐將一個裝了人的口袋拋向大海。這應是鄧蒂斯冒充死去的法利亞長老﹐藏在屍袋中伺機逃出監獄的情景。那時大姐已從執信高中畢業﹐考入嶺南大學。二哥革命
大姐入讀嶺南時﹐二哥早已進入中共東江游擊區﹐投身‘革命’ 去了。未幾﹐三哥也步二哥後塵﹐成了一名游擊隊員。但他們兩人性格頗不相同。
二哥是真誠的‘革命者’ 。他在廣州中山大學附屬中學唸書時﹐已積極參加學生運動﹐國民黨稱之為‘學潮’ ﹐其矛頭指向當局﹐口號是‘反飢餓’ ﹑‘反內戰’ ﹑‘反迫害’ 。這固然有人幕後操縱﹐但歸根結底源於抗戰勝利後﹐蔣介石手下的貪污腐敗﹐特務橫行﹐以致民不聊生﹐民怨沸騰。我們家生活富裕﹐絕無飢餓之虞﹐可是赤化宣傳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共產主義的烏托邦極富誘惑﹐追求理想的熱血青年無不膺服。連蔣的親信之最﹑‘文膽’陳布雷家﹐亦出了共產黨---陳最鍾愛的幼女陳璉及其夫婿均為中共地下黨員。故身為普通國民黨員的我父親﹐子女投共自不奇怪。
中大附中是廣州市內名校﹐與廣雅中學執省市中學之牛耳﹐而中共滲入兩校亦久。二哥有一同學名修﹐湖南人﹐出身知識分子家庭﹐在廣州長大。他1947年夏入中山大學未果﹐同年秋赴港考入達德學院﹐該校為‘民主黨派和愛國民主人士出面共同創辦’﹐實際為中共領導﹐為之培養幹部。入學半年後修進入東江游擊區﹐二哥時已入讀中山大學工學院化工系﹐1948年3月他托詞赴港﹐由修介紹﹐經達德學院前往該區。其另一摯友﹑附中同學雅亦為介紹人。
他們所在部隊前身為抗戰時的東江縱隊﹐1946年東縱主力根據國共雙方協議北撤﹐餘部後組建為粵贛湘邊縱隊﹐由尹林平領導﹔其中一部活動於增城﹑龍門﹑從化﹑博羅一帶山區﹐後稱東江第三支隊(東三支)。二哥即屬東三支。主要發動農民要地主減租減息﹐但有時也會跟當地土豪武裝或國軍交火。在一次戰鬥中﹐二哥奮不顧身﹐衝鋒陷陣﹐奪得敵方一挺機槍。戰後不久獲准加入中共﹐未幾更擢升為連隊政治指導員。
儘管如此﹐他與家裡仍保持聯繫。三哥造反
也是出於修的介紹﹐三哥於1949年3月從香港赴游擊區。但其後他的道路異於二哥﹐並沒有入黨﹑提(升)幹(部) 。究其原因﹐當在他兼屬‘造反者’ 與書生﹐對中共那套理論並非照單全收。他也曾在中大附中就讀﹐且成績不錯。可是具叛逆性﹐好挑戰現存秩序﹐視校規如無物﹐終離附中。後轉入長風中學﹐學業依然出眾。但因其心儀之某老師與校領導反目﹐他捲入其中﹐竟被開除﹐時距高中畢業僅一學期。他無心繼續學業﹐遂赴港居於大哥處﹐未幾與修邂逅﹐隨之加入東三支。其間也曾風餐露宿﹐他雖少爺出身﹐倒也能熬過去。不過其書生意氣﹐自由散漫﹐頗受人詬病。他甚至懶得揹槍﹐將之交別人代勞。
當年7月﹐他自游擊區赴港購物﹐在西環羲皇台與大哥同住。恰逢父親由穗來港﹐時共軍早已席卷寧滬蘇浙﹐勢不可擋。父親剖析時局﹐勸我大哥﹑三哥兄弟倆赴美留學﹐以應丕變。父子情深﹐自屬良言。無奈他倆俱受潮流影響﹐拒絕了父親的好意相勸。
其後數日三哥歸隊﹐當年10月下旬﹐與二哥先後隨軍凱旋﹐身穿‘解放裝’﹐回到已易幟的廣州。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