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文峰转自独立中文笔会
裴毅然:“反右”前毛泽东心态分析
作者editor
3月 9, 2021 反右, 毛泽东, 红色史褶里的真相, 裴毅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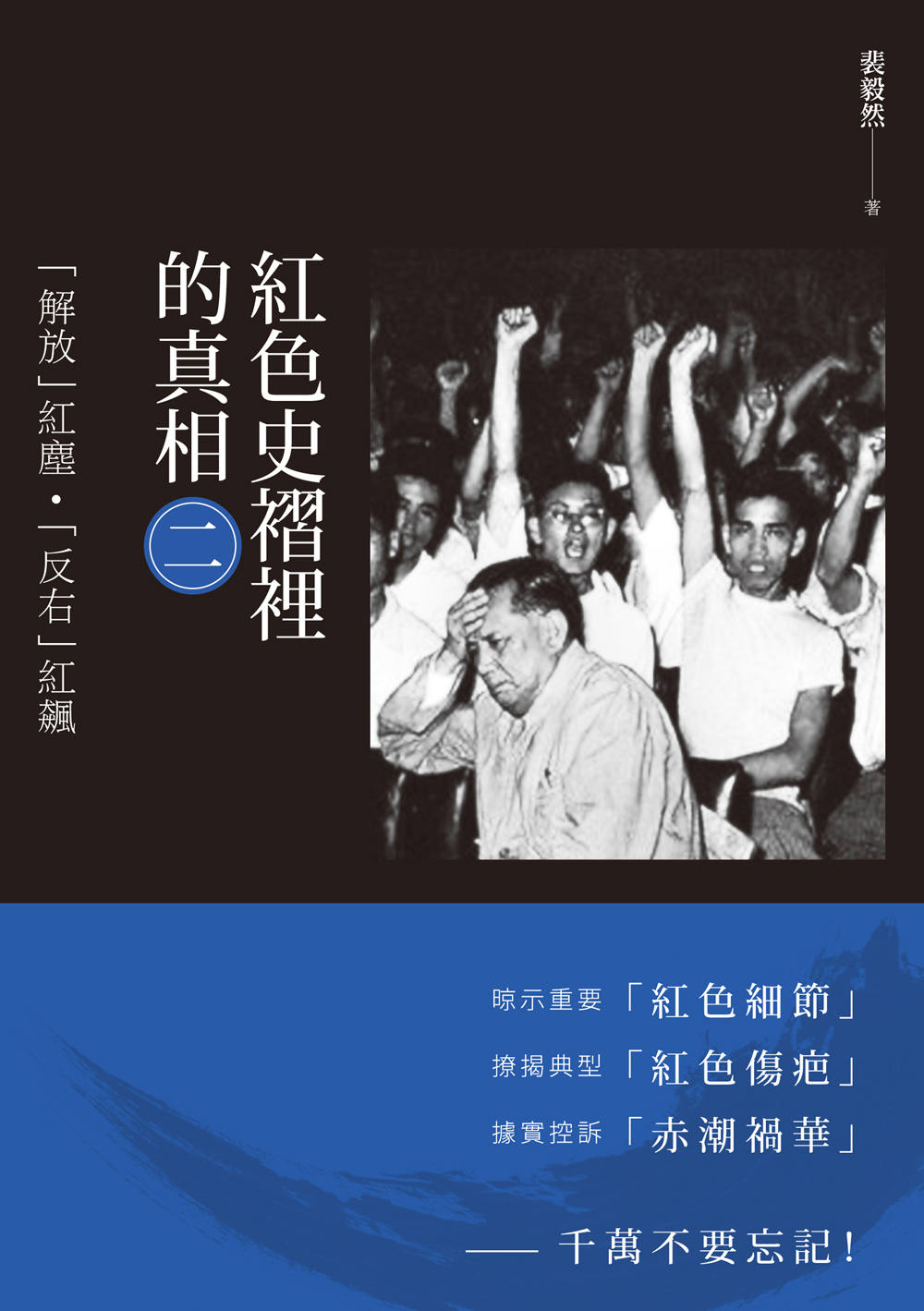
《红色史褶里的真相》第四辑 :“反右”红飙(1)
“反右”前毛泽东心态分析
“反右”运动影响深巨,成因诸多,直接祟源则来自毛泽东“圣心”一瞬。对此,史界争议不大。有争议的是毛泽东早有预谋的“引蛇出洞”(李慎之、李锐观点),还是中途“转折说”(于光远、朱正观点)。“引蛇出洞”派认为毛泽东1956年提倡“双百方针”就是撒布钓饵。“转折说”则认为毛听闻鸣放激烈的“反动言论”才转放为收,1957年5月15日为标志性拐点,向党内打招呼,传达〈事情在悄悄起变化〉。
2007年6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召开“反右五十年研讨会”,大右派章乃器之子章立凡(1950~ ),认为毛发动整风意在统一党内分歧,重振个人权威,未必早早定策“引蛇出洞”,但鸣放一起,水漫金山,毛因势利导一举实现打掉民主党派与反冒进的党内务实派两大政治目的,同时提升个人权威。[1]
无论哪派观点,从鼓励“鸣放”到以言定罪,由放转收,公然失信,弯子转得太大,举世惊怒,莫知所以。毛泽东这一时段的心态成为“反右”研究一大悬案。笔者至今无法理解老毛为何发难反右。无论政治必要还是自身信誉,实无理由如此失信天下。惟一可理解的只能是:中共根本不理解民主自由,他们的政治思维习惯“枪杆子里出政权”,延安整风也使他们习惯暴力镇压异见。1989年的“六·四”,也是在毫无必要的情况下动用暴力,与1957年的反右在逻辑上一脉相承。
2007年8月,李锐先生在《领导者》发表〈毛主席与反右派斗争〉,从毛早年政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开始,梳理毛泽东将知识分子划入资产阶级行列的思想脉络,引了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1950年6月)的讲话——
知识分子中的一个相当多数,与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政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崇洋媚外、媚美,与我们格格不入,必须进行思想改造。
1956年6月波兰事件、10月匈牙利事件,李锐认为毛深受刺激,“从这时开始,他就着意考虑怎样避免中国发生同类事件的办法了。”李慎之先生(1923~2003)也持这一观点。按二李逻辑:毛泽东一向视知识分子为敌,见波兰、匈牙利知识分子闹事,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早晚也会闹事,合作化运动确实引发一些“叽叽喳喳”噪音,因此放出大手笔“引蛇出洞”,让毒草冒出来,然后举锄铲之。先让知识分子放出“右派”言论,放出各种对中共的不满,然后指举为证,发动“反右”,将民盟为首的知识分子政治势力彻底打下去。二李认为如此这般,毛泽东“反右”前一系列诚邀批评、动员“鸣放”,以及何以大转弯,才能得到顺理成章的解释。
不过,二李观点乃逻辑推导,不太经得住质证:既然定策“引蛇出洞”,何必远兜远绕这么大一圈?尤其公然失信天下,政治形象大失分。最麻烦的是:得做两次方向截然相反的社会动员——先鼓励鸣放“言者无罪”、后大力反击“以言定罪”。如此悖反的政治大动作,势必引发思想大混乱与社会大动荡,镇压一批人自然多一批敌对者,不到万不得已,何必主动树敌?统一战线可是毛泽东玩得最拿手的,这几粒算盘珠,63岁的毛泽东不会扒拉不清。再说镇压士林要得“暴君”之号(方毅1980年中共“四千人会议”上即指毛为暴君)[2]。毛泽东一向自视甚高,放着一代明君不当,去当肯定“要上书”的暴君,一开始就直奔秦始皇而放弃李世民,符合常态心理吗?符合写下气度甚伟的〈沁园春·雪〉的雄主心理么?
笔者认为:毛泽东确有讨厌知识分子的“北大情结”(毛曾为八块大洋的北大图书管理员),也有视知识分子为敌的一贯意识——将知识分子划归资产阶级,1949年后说过一系列厌恶知识分子太吵太烦的“语录”。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委书记会议上有几段狠话——
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他们有这么一些思想,过去没有讲,百家争鸣,让他们讲,这些话就出来了。……他们现在要出来,大概是要扫我们了,是不是想复辟?
……我们敢于改造资本家,为什么对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不敢改造呢?
社会上的歪风一定要打下去。无论党内也好,民主人士中间也好,青年学生中间也好,凡是歪风,就是说,不是个别人的错误,而是形成了一股风的,一定要打下去。
有些民主人士和教授放的那些怪议论,跟我们也是对立的。他们讲唯心论,我们讲唯物论。他们说,共产党不能管科学,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合作化坏得很;我们说,共产党能够管科学,社会主义有优越性,合作化好得很。
学生中间跟我们对立的人也不少。现在的大学生大多数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其中有反对我们的人,毫不奇怪。这样的人北京有,石家庄有,其他地方也有。
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而教育人民。……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
确实可嗅出毛泽东的“反右”脉跳,含有“引蛇出洞”的意图。但是,同篇讲话中,毛泽东也说了不少反证语:
不怕闹,有精神准备,才不致陷于被动。我看要准备出大事。你准备出大事,就可能不出,你不准备出大事,乱子就出来了。
只要不犯大的路线错误,全国性的大乱子是不会出的。即使犯了大的路线错误,出了全国性的乱子,我看也会很快平息,不至于亡国。[3]
根据这一时段毛泽东一系列讲话的综合情况,毛从产生“反右”意图到实施反击,有一思想发展形成过程,即从犹豫到决定的酝酿过程。匈牙利事件见报后,毛泽东写了两篇语气磅礴雷霆万钧的《人民日报》社论——〈论无产阶级专政〉、〈再论无产阶级专政〉,一再强调必须百倍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中央布置,全国学习,〈两论〉持续学习了半年(直至1957年4月),且与以往运动不同,一不停课停业、二不搞人人过关,似乎只要国人反复认识“无产阶级专政要加强”,显然意在加强压力,要知识分子识相点——“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吃素的”。这当然也从逻辑上符合稍后的铁拳“反右”。
毛泽东最终决定下手收拾知识分子,乃多因之果。二李先生确实指出了毛泽东之所以发动“反右”的心理动因与思想脉络,但真正触发启动这些基础因素,将思想认识转化为政治大动作,尚需最最重要的现实因素。毛泽东最后下决心“反右”,直接因素是对形势的判断,即对“鸣放”的形势判认。
毛泽东确有规避波匈风险的“远见卓识”,希望早作准备早行预防,但波匈事件终为外因,至多投下心理阴影,提醒他“知识分子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不满”,决定因素还是国内政治态势。1949年执掌国柄后,从1951年思想改造到胡风案后的“肃反”,已大大抽紧知识分子脊梁,虽有一点“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党政不分”的刺耳声音,毕竟嗡嗡如蚊,低弱边远。毛听到的主要声音还是大分贝的谀颂。开国七年,中共“一时气象”,大多数国人尚陶醉在“东方红,太阳升”的幸福中。所谓“知识分子闹事”,不过一些量级很低的不同意见,并无高分贝的“恶攻”,更无现实行动。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做了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戳到毛泽东最痛处,他不愿一世令名得到斯大林的下场,形成“〈秘密报告〉情结”,因此提出“双百方针”。
毛泽东的“双百方针”,着眼点在于规避波匈事件与“秘密报告”,希望解决知识分子问题。他明白对付士林,除了镇压,还有一条更佳途径——让他们把话说出来、把屁放出来,说了放了痛快了,就不会惦着去闹事了。因此,“让说话”也是解决知识分子问题之一途。从正常心态来分析,毛泽东提倡“双百方针”,鼓励鸣放,还是想当明君,各项工作的提高确实也离不开批评。再说,让知识分子说话,知道他们在想些什么,洞悉民心明了下情,也是雄主明君(更不用说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应有气度,唐太宗都能做到,我毛泽东还不能么?同时,他也要做给反对“双百方针”的赫鲁晓夫看:我毛泽东不像斯大林压着捂着,知识分子的“屁”当面就放出来了,身后不会有人做我的〈秘密报告〉,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可是真民主。一箭数雕,何以不为?
1957年春,毛泽东邀请周扬、林默涵、邵荃麟、张光年、严文井等红色文化人入中南海颐年堂座谈,周恩来、朱德等中共要角出席。毛泽东着重阐发了“双百方针”,批评了四位部队文艺官员——陈其通(总政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总政文化部副部长)、马寒冰(总政文化部文艺处长,6月28日因划“右”自杀)、鲁勒,保护了当时挨批的王蒙。午餐后,毛泽东单独与《文艺报》主编张光年谈话,张有一段记述——
主要意思是对一般有错误观点的文章和作品,要一分为二,批评时也指出他多少还有对的地方。我很受感动。我们都认为他要认真推行双百方针,接受了斯大林的教训。我们佩服他博学,懂得如何处理各种社会矛盾。1957年春天《文艺报》(周刊),正是在这种气氛下应运而生的,完全没想到会有所谓“1957年夏天形势”。[4]
根据张光年这段记述,实在不合“钓鱼说”。
然而问题在悄悄起变化,鸣放一起,很快听到最不愿听到的言论——“党天下”、“小知识分子统治大知识分子”、“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高明”、“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 知识分子确有“异心”,对国家大事确有不同设想,中共一系列政策受到根本质疑,权威遭到极大威胁。北京师范大学出现这样的大字报(全文)——
1949年至今已八年,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宪法也颁布了。有脑筋的人想一想,民主生活是否充分?答案是否定的。所谓“民主”者空有其名。人民除物质生活有保障外,其他一切民主权利概无保障,党独揽一切,专断一切,党即人民全体,党即国家,党即法律。所谓“民主”者实际上已被党主所代替。
略举一二事例——
宪法规定人民有选举权,然而人民代表已由党内定。人民不认识代表,代表不认识人民。
宪法规定人民有言论自由,然而报刊、广播、电台均为党所垄断,凡发表有与党的调子不谐和的言论,概以反革命论罪。
宪法规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自由,然而凡结社、集会不经党批准、并接受其指定的领导人,均有可能冠以反革命罪。
宪法规定人民有人身自由,然而“肃反”表明:各级党组织负责人都有权以党的名义,限制任何一个正直的公民的自由。
毛主席说现阶段我国政权性质是人民民主专政,然而党包办垄断一切,民主党派只是充当傀儡,人民民主其名,一党专政其实。
党的中央委员会是1200万党员的代表大会选举的,然而党中央向全国六亿人民发号施令,人人均得服从。
宪法规定政府向民主机构人民代表大会负责,然而实际上政府的一切政策均由党来决定,政府只对党负责,人民代表大会空有其名。
我们是要党的领导,但坚决反对党独断独行。我们不反对“党主”(因党也有作主权),但反对以“党主”代“民主”。把民主权给予人民,让人民有享受宪法所赋予的民主权利的充分保障。[5]
此时,毛泽东才意识到赫鲁晓夫拦阻“鸣放”的政治远见,才真正意识到“专政”的必要性,才横风断缆,由放转收,出手镇压。毕竟,维护“专政”是压倒一切的基本面,镇压社会主义的敌人不可手软,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再说,老毛一向“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为了“宏伟的社会主义目标”,只能当秦始皇了。6月8日,毛以中央名义致函各省委、自治区党委:“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他还不用论据地说:“国际形势很好,美国处于困难地位。”[6]
综上所述,尤其根据心理常态,笔者认为毛泽东最初不可能没有当“明君”的心态,指说毛泽东早有“引蛇出洞”的预谋,缺乏有力史料支撑。于光远(1915~2013)也不同意“引蛇出洞”,于先生认为毛泽东1958年武汉会议上说布置引蛇出洞,乃是掩盖料事失准,屏蔽“鸣放”失算,强撑胸有韬略指挥若定,事后诸葛耳。[7]
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1896~1984)——
在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开始时,毛泽东同志并没有提出要反右,我也不是为了反右而开这个会,不是“引蛇出洞”。两个座谈会反映出来的意见,我都及时向中央常委汇报。五月中旬,汇报到第三次或第四次时,已经放出一些不好的东西,什么“轮流坐庄”、“海德公园”等谬论都出来了。毛泽东同志警觉性很高,说他们这样搞,将来会整到他们自己头上,决定把会上放出来的言论在《人民日报》发表,并且指示:要硬着头皮听,不要反驳,让他们放。在这次汇报之后,我才开始有反右的思想准备。[8]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一个急转弯,突然鸣“收”,与此前的“鸣放”彻底背反,党内外一片哗然。宋庆龄致信中共中央——
党中央号召大鸣大放,怎么又收了?共产党不怕国民党800万大军,不怕美帝国主义,怎么会担心人民推翻党的领导和人民政府?……一些二三十岁的青年知识分子怎么可能一天就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我很不理解这个运动。我想了两个多月,还是想不通;有这么多党内党外纯粹的人,会站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立面?要推翻共产党?[9]
北师大俄语系学生述弢(1938~ ):
从广开言路、鼓励鸣放到舆论一律、实施反击,这个弯子转得实在太大。但因为是党的号召,“金口玉言”,我辈便紧跟犹恐不及,一味责备起自己来了。[10]
可见,上上下下对如此突转弯子,都无心理准备,都感觉“不自然”。
根据常识,“反右”如此大规模的政治动作,又几乎出于毛泽东一人运筹,心理应该十分复杂,原因诸多,不可能简单一因。“二李”分析为单一原因,显失妥当。当然,最根本的因素还是文化问题,即毛泽东长期浸染东方专制文化,只熟悉“鱼肉刀俎”的专政,不认识“熊掌与鱼兼得”的民主,心理承受能力太弱、容异度太低。毛一生玩政治,只熟悉尔虞我诈、你死我活,只知矛盾的对抗性,既不习惯民主的“多元共振”,更不理解民主的价值——调动社会成员积极参与公务,从而集智于众,民主必须伴随舆论多声部。哲学上,也不理解矛盾的“同一性”远远大于高于“斗争性”。毛泽东一听“叽叽喳喳”,与只熟悉“一言堂”的各省市官员一样:这还得了!这不是反革命要翻天吗?将走向民主必须的不同意见不同声音判为绝对不能容忍的“反革命进攻”。
九位省委第一书记致电中南海,要求限制“鸣放”,但他们还不敢提出“坚决反击右派进攻”。[11] 赵紫阳其时也不习惯“鸣放”——
一让提意见,各种意见铺天盖地,有的很尖锐,这大大出乎他(指毛)的意料。我当时在广东管农业,座谈会上一些人指着鼻子骂,真受不了呀!后来接到中央电报,说要“硬着头皮顶住”,邓小平也到广东来做报告,说放长线钓大鱼,那就是打招呼准备反右派了。对当时的大鸣大放,各级干部有意见……共产党各级干部都没学会听取不同意见。[12]
土改、镇反、知识分子改造、三反五反、批胡适、批胡风、肃反等一系列运动,民间积累的怨气确实不少。但就当时“右派”的整体质地,想要推翻中共政权的“反革命”绝少,大多数国人对中共的红色图纸尚存寄望,尚不可能慧眼穿赤。就算想要打倒中共,难道就这么放几句“毒”,几百万“解放军”是吃素的?
至于“反右”的恶劣性,从思想上划分阶级,不仅回到封建文字狱,还增加了一项现代“思想犯”,为大规模镇压知识分子提供了“方法论”——可以根据“莫须有”的思想推测定罪。尽管毛泽东已意识到阶级论有偏差,放出大逆之言:“马克思主义就是个扯皮的主义,就是讲矛盾讲斗争的。”[13] 但估计毛泽东没想到会打出这么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但既然大力提倡反击右派,气可鼓不可泄,只有硬着头皮在政治上“一面倒”,接受“扩大化”。为维护“反右”正确性,唱出“右派分子想翻也翻不了”。
直至“四人帮”倒台,文革结束,赤色意识形态才被踩刹车。这场旷时持久的“赤潮祸华”,根本之因还是文化问题——中共党人没有能力辨识马克思共产设计的乌托邦之弊。如此天翻地覆的社会改造,仅凭马恩理论设计与苏联片面信息,便认定“最新最美”,借助政治暴力强推硬销公有制、计划经济。然而公有制既悖扭人性,也违反“观俗立法”历史理性,整一个南辕北辙。行至文革,连中共高层都沸反盈天。最后只得返身走回头路,迎回“万恶之源”的私有制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了马列主义,中共迫使中国缴纳高昂学费。
具体到毛泽东个人,虽然老毛一直指说别人不懂马列,全党没几个人懂马列,其实他自己对马列也不甚了了。李德:“毛泽东的马列主义知识十分肤浅。这是我对他的印象,博古也同意这种看法。”[14] 二李先生也说毛可能终身未通读《资本论》,床头多为线装古籍,封建的东西远比马列装得多。当然,马列主义本身亦为谬说,充其量为一种社会学说,提供一种社会改造方案,需要实践检验。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捏着举着自己也一知半解的学说当绝对真理,只准膜拜不准质疑,只准照办不准修正,只准赞扬不准批评,绝对教条+暴力专制,当然只能制造赤灾巨祸。
中共开国后的所谓“一边倒”学苏联,其实自己也不知道怎么搞社会主义,只能照着人家葫芦画瓢。如此缺乏经验支撑的社会大变革,又完全鄙视历史理性凝结的传统,不承认各种客观条件的现实制约,所谓天翻地覆的社会主义改造,真正盲人瞎马,夜半临深池矣!“反右”又打掉士林发言权,国家失去理性滤网,由大跃进走向大饥荒,由“七千人大会”走向文革,实为赤色思潮与独裁专制结合的一种历史必然。
“反右”罪责自然非毛莫属,毛泽东执国柄一言九鼎,其认识能力与政治气度也就成了最根本的制约因素。他认定“右派”乃是推进社会主义的阻力,有碍他的“敢叫日月换新天”,必须镇压。如此这般,“反右”便成了“历史前进的必然”,他也只能自认秦始皇。
对比历史,个人作用之强、能量之大,毛泽东远超秦始皇,他为此十分自豪。“反右”对毛泽东晚年心理影响甚大——既然已成“秦始皇”,一不做二不休,干脆硬撑到底,走向极端。否则,怎会上演文革大戏——再演残杀功臣的历史老剧?
不过,如此公然失信,如此不顾忌政治形象,虽然达到“专政”目的,毕竟以支付道德信誉为代价,毁损的不仅仅是中共本身,全社会走向虚伪化。“反右”以后,虚矫伪饰堂皇出行,人人必须戴上面具,全社会运行在虚假之中,一切价值基点都倾斜了,失去正确立论的前提,越走越偏,国家长达二十余年生活在恐怖之中,人人自危。中共中央调查部副部长王涛江(1915~1995)——
这桌子上原本没有茶杯,偏偏说这桌子上确实有一个茶杯,有时还会把桌子上的杯子说成是茶壶。[15]
“反右”后,一句“请提意见”,立刻使人不寒而栗,马上联想到“钓鱼”、“引蛇出洞”。君子视政治为畏途,小人揣着明白装糊涂,培养出一大批只会宣誓不说真话的各级官吏。2007年11月22日上海白天鹅宾馆810室,著名“右派”朱正先生提醒笔者:“两个人说话可以随意,三个人说话就得注意。”人心如此,国家自然只能走向现代化的反面。“反右”实为反真,贻祸之烈,悬垂至今。读书人只能一声潼关长叹!
至于毛泽东的历史评价,虽然今天“尸在堂,像在墙”,毕竟“已悬一线”,距离彻底清算的“最后审判”不远了。很简单,老毛的所有政治逻辑都被推翻:抗美援朝、三反五反、三大改造、肃反反右、三面红旗、十年文革,无一“正能量”,无一能够继承,连金光闪闪的“毛泽东思想”都被请出“指导思想”,除了等待审判,老毛还有什么值得国人“永远怀念”?
[1] 金钟:〈悲怆的历程——普林斯顿反右五十年研讨会散记〉,《开放》(香港)2007年7月号,页46。
[2] 李锐:〈毛主席与反右派斗争〉,《领导者》(香港)2007年8月号,页97、101。
[3]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7年,页333、337~338、350~355。
[4] 張光年:〈回憶周揚〉,王蒙、袁鷹主編:《憶周揚》,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頁11。
[5] 天、水、心:〈民主乎?黨主乎?〉(1957-6-6),俞安國、雷一寧編:《不肯沉睡的記憶》,中國文史出版社(北京)2006年,頁318~319。
[6]《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7年,頁432~433。
[7] 李慎之:〈對反右派鬥爭史實的一點補充〉,《李慎之文集》(自印本),頁196。
[8]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1986年,下册,页833~834。
[9] 宗凤鸣:《理想·信念·追求》,环球实业(香港)公司2005年,页239~240。
[10] 述弢:〈哭泣的青春〉,俞安国、雷一宁编:《不肯沉睡的记忆》,中国文史出版社(北京)2006年,页78。
[11] (英)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376。
[12] 王扬生:〈叩访富强胡同六号〉,《明报》(香港)2005年1月30日,A4版。
[13]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7年,页344。
[14] (德)李德:《中国纪事》,李逵六等译,东方出版社(北京)2004年,页67。
[15] 魏小兰:〈“我信天总会亮”——康生秘书谈“沙韬事件”〉,《百年潮》(北京)2007年第9期,页56。
初稿:2007-5~6;增补:11-22。
原载:《领导者》(香港)2007年第6期(删削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