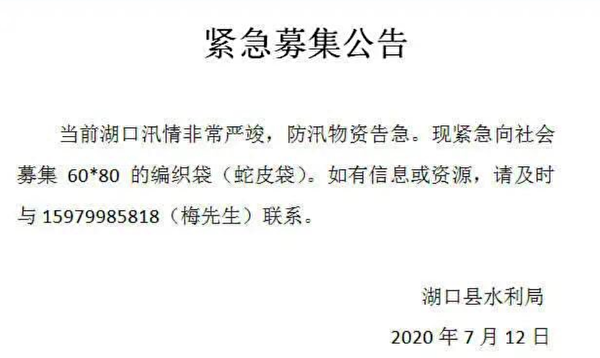孙天星 转自 纵览中国
我的母亲叫年静甫,排行老二,姊妹三人,陕西汉中人,据说是年羹尧的后裔。母亲和大姨上学时,大姨的老师是地下共产党,把大姨及班上大部分学生偷偷带去延安。大姨把在延安抗大的照片寄给还在上学的母亲。她穿着灰军装,戴着灰军帽,腰上扎着牛皮带,皮带上别着一把小手枪,很威风。母亲把姐姐的照片给同学们炫耀,后来校方追查共产党活动,才赶忙收起来。
母亲长得很漂亮,后来和在中央军校第一分校(汉中)当队长的父亲结了婚。据说母亲很羡慕父亲穿着马刺走路的样子,又说是母亲在回家的路上被巡警刁难,恰巧父亲路过,为母亲解了危。
解放后我一直没再见到父亲,也不知他在那,更不知他的死活。有时见母亲偷偷包点莫合烟和裤衩之类的东西托人带走,我就想父亲大概没死。
母亲个子高,嘴长得比较大。每当坐在母亲对面,望着她把一团十分粗糙的食物放进嘴巴的时候,我就想知道这些粗糙的东西在经过一个坐过飞机,穿过旗袍,做过太太,细皮嫩肉的母亲的喉管时,母亲的心理是怎样的。
上小学时,我见别的孩子有钢笔,就央求母亲给我买一只。母亲一声不吭,嘴抿得紧紧地,泪水从眼眶里滚出来。我不懂事地继续央求,邻居阿姨一把把我拉开,对我说,傻孩子,你妈妈哪有钱呀。后来稍大一点,才知道母亲整夜整夜偷着给人家做衣服,很少睡觉。做一条裤子才8毛钱。那个年代是绝对不允许做私活的,也不允许凭个人劳动挣钱糊口。可是,母亲一个女人要养活五个孩子呀。现在想起来,当时的央求简直就是一种罪过。
我家在草湖,位于疏勒、疏附和阿克陶三县交界处,解放前叫马家花园,原是一片长满芦苇、红柳、骆驼刺等多种野生植物的原始荒原,东西长约二十公里,南北宽约十五公里。塔孜洪河和罕南里克河将草湖分割成三块,分别是小草湖、大草湖和红柳戈壁。民国初期,喀什提督马福兴在小草湖为他建造了一座花园式的豪华公馆,占地百亩,当地人称为马家花园。1924年,新疆都督令马绍武清除马福兴,马家花园毁于战火,成为一片废墟。解放后,马家花园成为兵团一个团场的驻地。
我上学的地方离家有七十多里,由于没有交通工具,很难回一次家。每次回家都是约上几个家住草湖的同学,星期六放学吃完晚饭后结伴往家走,双脚在没脚脖的尘土中移动着。没有星光的夜晚,大家一边走一边唱歌,以消除心中对黑暗的恐惧,每次到家都是半夜了。现在想起来,也不知当时那么艰难地回一次家是为了什么,可能是为了看一下艰辛的母亲,也许是为了回家能吃一顿饭。
六十年代,吃饭可能是最简单、最重要的事情。家中没有吃的,最好的食品是公家配给的一种叫代淀粉的东西。先把玉米芯碾成粉,然后将其发酵,然后再过滤、烘干、碾成粉,是谓代淀粉。这种粉可以做成食品,可以吃,但不好吃。它是优点是可以饱肚子,缺点是吃完后肚子发胀,硬硬的,鼓鼓的,更要命的是大便十分困难。每次回家,母亲总是让我多吃几个这种代淀粉馍馍。母亲说我正在长身体,要多吃点,吃好点。其实我知道,即便是这种东西也是定量配给的,我吃了,母亲就没得吃的了。小时候不懂事,为了自己的嘴巴,而忘了生我养我的母亲。现在长大了,是该自己掌自己的嘴巴。
有一次回家是为了问如何在初中升高中的履历表中填写父亲一栏的内容。母亲坐在那一声不吭,好像进入了深深的回忆,又好像什么也没想,一动不动。我央求母亲说点什么,结果她什么也没说。最后我凭记忆和想象,自作主张填写了四个字——大官,坏人。
文化大革命中,母亲吃尽了苦头。在批斗母亲的风头上,我回了一次家,为的是想告诉母亲,我要结婚了。破烂小屋门口的炉灶被踢得稀烂,我以为母亲搬家了。趴在门缝中往小屋里望去,依稀可以看见床和被褥。我很慌,也很急,开始无目标地寻找母亲。突然,我看见几个人提着鞭子,赶着一长串“牛鬼蛇神”过来了。我从头到尾仔细看去,发现走在最后面走不动的就是我那可爱又可怜的母亲。一个拿鞭子的朝我母亲屁股上踢了一脚,母亲痛苦地朝前倒下。我冲了上去,可是一个人拉住了我。我回头一看,并不认识他。等我转过身时,那几个拿鞭子的和那一串牛鬼蛇神全不见了。
天渐黑了,我敲了一个阿姨的门。她很害怕的样子,说了声不知道,就赶忙把门关死了。我又敲开一个叔叔的门,他也惊慌地说不知道,忙把门关死。
天黑得像一口锅扣在大地上。我一个门一个门地敲,谁也不给开门。一个门内忽然伸出一只手把我拽进了进去,像蚊子叫一样说了声“你妈在狗屋里”,随即把我推出门外。我没有时间思考,飞一般地向狗屋冲去。狗屋原是一个养军犬的地方。我一脚踢开狗屋门,十几双惊慌的眼睛望着我,小声说:“你妈回去了。”我急忙跑回那破烂的小屋,一丝灯光从黑帘中透出。我轻轻地敲了一下门,母亲惊慌地问是谁。当确信是自己的儿子时,她开门将我一把拉进去。母亲告诉我,未成年的小妹已经藏起来了。几年后一个阿姨告诉我,说这期间母亲曾两次触电自杀未遂。
母亲的后半生也有过几次微笑。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家养了两只兔子,下了一窝小崽。小兔子长大一点时,母亲决定杀一只叫孩子们尝点肉味。两个弟弟负责这件令全家人喜出望外的事情。可是两个弟弟不太积极,因为兔子主要是他俩拔草喂大的。为了全家人能吃上一次肉,他俩无可奈何地在兔子头上敲了一下,把兔子敲死,然后挂在树杈上开始剥皮。他们先把兔子嘴边的皮割开,然后是头,脖子,最后紧紧拉住兔子头上的皮毛,使劲往下一拽,整个兔子皮就被脱下来了。就在弟弟把兔子皮从头到尾往下拽的那一瞬间,母亲笑了。这一瞬间,她似乎忘记了贫穷,忘记了烦恼,忘记了曾经受过的羞辱。我想母亲的微笑起码包含着两个意思:一是自己的孩子今天有肉吃了;二是两个小家伙长大了,可以干活了,不会饿死了。
我上初中时发表过一篇小散文。大妹妹在未成年时就下地干活了,放暑假时我去大田看她,她正在摘瓜。兵团是条田化作业,大条田里遍地都是瓜,摘下的瓜堆成小山,香气四溢,蜜蜂飞舞。那天我吃了好多瓜,大开了瓜的眼界。回校后,瓜的香味依然包围着我,于是在作文课上我写了一篇名曰“瓜田小记”的散文。文章不长,但写得很有生活气息,老师叫我抄好送报社。文章发表后,草湖的好多人都看到了,他们向母亲祝贺说:“老年,你儿子这么小年纪就发表文章,将来不得了。”母亲大概高兴了好几天。这是母亲的第二次欢喜。
母亲最后一次微笑是在病床上。经过长期批斗,母亲倒下了,任何鞭子也打不起来了,当时我在离家五百公里的农村接受再教育。再教育不是让你读研读博,而是让你天天干繁重的体力活,滚一身泥巴出一身臭汗,进行触及灵魂的劳动改造。有一天,有人跑来说,草湖来电话了。我急忙跑到公社,把电话打到草湖总机。总机说,你们家已没人了,都到毛拉医院去了。我知道毛拉医院就是师部医院,离我这有八百公里。我马不停蹄,坐汽车,坐拖拉机,坐马车,再步行,心急如焚地赶到毛拉。母亲己不省人事,弟妹们在床前一面呼唤一面哭泣。医生把我叫出来说,你母亲没有几天了,准备一下吧。我忍着塌天的悲痛,白天守在病床边,等待奇迹出现,晚上用缝纫机给母亲做老衣。我虽然只跟母亲学了一点缝纫技术,但我一定要“下定决心,排除万难”,让母亲穿上儿子亲手做的衣服,尽最后一丝孝道。
人急时总有急时的办法。我们几个孩子首先央求医生给母亲输血,医生说输也没用。我们一再央求,医生最终答应试试。化验结果,我和二弟的血型与母亲的一样,都是B型,于是当场各抽了500CC给母亲输进去。第二天奇迹出现了,母亲睁开眼睛了,看见了自己的骨肉。我和二弟又各抽500CC给母亲输上,更大的奇迹出现了,母亲坐起来了,微笑地望着五个孩子。这是母亲最后的笑容,这个笑容太美了,太珍贵了。这是战胜死亡后的微笑,我留下了母亲这个最后的微笑,这是母亲活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张照片。
医生用肯定的语气高兴地说:“你母亲还可以活半年,你们可以放心地回去工作了。”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母亲。五个月以后,也就是文化大革命进行到第八个年头时,母亲死了。她永远看不见她含辛茹苦养育的孩子了,孩子们再也看不见可爱可敬可怜的母亲了。我们把母亲埋在草湖的沙丘里。我们成了孤儿。我的母亲只活了四十八岁。
补白:刘某是东南沿海某省会城市一家木器厂的老炊事员,孤寡一人住在厂里。这天晚上因暑热难熬,跑到河边公园纳凉。躺到半夜,准备回去,听见牌楼上有叽叽喳喳的麻雀叫。他到河边抓几把河泥,向牌楼掷去,想打中几只麻雀,回去炒了吃。第二天一早,一个清洁工看见牌楼上的伟大领袖像上粘着什么东西,便赶忙叫来几个工友。大家仔细一看,吓傻了,伟大领袖满脸污泥。案子立刻报到市革委会,革委会主任拍案而起,下令马上封锁道路,严禁人员过往,强行通过者和传播该事者格抓勿论,同时迅速组成专案组。案子很快真相大白。市革委会在广场上召开万人宣判大会,刘某五花大绑,奄奄一息,被拉上审判台示众,吓得魂不附体,一次次瘫倒。大会当场宣判刘某“恶毒丑化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的光辉形象”,实属滔天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本拟判死刑立即执行,后考虑其出身贫民,认罪态度好,死罪可免,但活罪难饶。服刑期间,刘某因身体极度虚弱,精神崩溃。一天野外劳动时,疯疯癫癫地跑出了警戒线。看押人员抓回来一顿拳打脚踢,当场断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