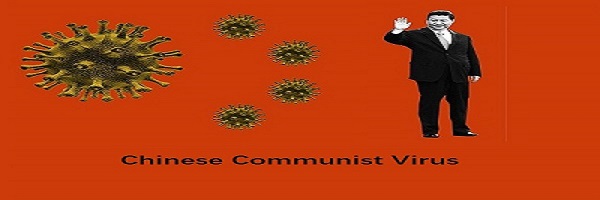李华平转自博讯新闻网
基督教思想中的“苦难”意识/王旭东
在“西方—基督教”思想传入之前,中国人已经适应了在“儒释道”三角心理结构中应对个体和类的苦难问题,这种关系可以是互补或者排斥的。儒家思想致求于扩充自己的生命潜能,敢于用积极姿态去对抗“无道”,并且重视一种社会关怀。通过自我道德的超进试图同时补赎个人偶在和历史灾难,的确赋予儒者一种奇妙的张力:比如颜回“陋巷”之乐和曾子“死而后已”的悲壮——两种差距迥远的信仰气质都获得了孔子极大的称赞。
但是这种模式依然是有重大缺陷的:比如陈龙正说:“上士贞其身,移风易俗;中士自固焉而已;下士每遇风俗,则身为之移。”因为大多数人在主观上都缺乏一种道德的自我扩充能力,所以终于不免沦于“下士小人”,而为苦难所吞噬。另外,儒家社会关怀的承诺竟慢慢变成了它自身的理论包袱:“罗汝芳问张居正:‘君进讲时果有必欲尧舜其君意否?’张沉吟久之,曰:‘此亦甚难。’”可见,当儒家开出的“治国、平天下”策方变成一张空头支票时,更加重了儒者的悲哀。余英时先生讨论过明代儒教运动已经基本放弃“致君尧舜”的宏观关怀,变成一种自我修炼的实践型宗教;我看儒学的关怀对象由“外济”变为“内得”之转变还要推早到王安石变法失败之后。
极其敏感于“苦”的佛教竟然会被据说是“乐感文化”的中国文化接受,实在是一件表面上看起来很不可思议的事。当然佛教汉传后也有教义上的调整,但其义理出发点依然是认为人生的本质是苦,只是因为起了迷妄计量,贪爱执著的心理,所以才执幻成真,误苦为甜了。所以佛教许诺通过修行能够怯除无明,得大解脱。佛教思想虽然精致,但对于没有印度哲学基础的中国人来说,如果严肃地追问之,会感到十分奇怪或者反逻辑的。比如对于“苦”的定义就有分歧,中国人看重而享受的世间情法(比如亲情友情爱情……)在佛教看来都是妄情计著、贪瞋痴业种变现,犹如毒蜜,这是中国人的良心常识所难以接受的。
道家思想也是属于思辨宗教的解脱模式。《道德经》愿意主动拥抱苦难,“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常德乃足,复归于朴。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因为这是符合居下处卑的“道”的本质的。但合归于“道”,对于个体来说,有什么终极意义?《道德经》没有给出连贯的解答,所以“道”信徒对于《道德经》可以有很个性的解释,而且与其他思想资源结盟的便利也很大。《庄子》在《大宗师》篇中(诗意地)解释说造化流转,锻阴炼阳,人如果适于造化,“安时处顺”,就可以得大自由。某种意义上来说,道释观都缺乏整体救赎意识,而且对于个体悟性的要求过高;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只是希望从中汲取一点神鬼玄通之力来规避或者减少生活的风险,根本不愿意从终极意义上去诠释人性的困境。
“西方”思想和“基督教”传入的不平衡特点使得中国青年不断地经历新的兴奋和迷惑。在晚清民初,抽空了“基督教”的西方义理所带来的更多是“喜乐进步”的情绪,很多中国思想家去提炼西方思想中关于“苦难”的命题,鲁迅也许略有兴致地窥探过尼采的“超人”如何用高贵的精神来藐视痛苦。尖锐的疼痛,绝望的悲伤……如何在悲剧艺术里完成意义的自我转化,变成一种生命审美。但是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种歇斯底里的“狂醉”是莫名其妙的,与自身的生命体验是陌生的……直到“文革”结束,中国青年方才奇怪地与西方世界的情绪在共时层面上接轨,就是分享关于人性、理性和整体价值破碎后的失望情绪。也是在这时,与欧洲一起经历了悲哀的基督教思想也渐渐传播进来,并且它的教义似乎也显得不那么轻浮和廉价了。
已经被去传统化教育基本剥夺了“三角心理结构”的中国青年现在可以比他们的爷爷辈更加从容地考量基督信仰的内在基础,并且向它提问了:基督教信仰带给中国青年的第一个印象也许就是它的教义(比如神子在“十字架”上受死)在功利主义情境中显得如此笨拙和迂腐;第二个印象依然是在功利主义情境下神本身的失败(比如如果神是万能的,为什么还有苦难和罪恶?)。在中国人的想象中,西方的神既然许诺比土著的仙佛更大的神通和权威,那么自然应该带来更大的福利才对了。
经过很长时间,第一批文革后的知识分子基督徒(还有“文化基督徒”)才开始明白,不是基督教义(或神)愚蠢,而是中国人在无神论或者假宗教的环境中生活太久了,当他们向基督教质疑时,已经选择了一个“人义论”的错误前提,基督教的传入也许可以洞照中国人思维方式中的一些盲区:基督教在什么意义上慰藉了西方世界的苦难呢?基督教是否可能慰藉中国的“苦难”呢?舍勒试图从追寻受苦意义的途径来解答苦难何以在神义论的前提下依然必要的问题,而这种意义,来自于神本身。“如果我们对于上帝理念和上帝存在,并非通过一种自上而下的模式,即是从精神的位格核心出发,依靠它与神圣的善和智慧的个体关联来获得,而是想自下而上,从我们熟悉的世界的性质,依靠因果推论来获得,那么即便整个世界都闪耀着和谐之光,只要存在着一丁点的痛苦感,我们就足以推翻一个‘至善’全能的造物主的存在。”神在“十字架”上的死,恰恰是自上而下的一种对于“苦难”的赎买。正如济慈所吟的:“世界是造就灵魂的峡谷”。正是由于有对世界悲凉的感悟,才能深切体会到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的用心良苦。
舍勒指出,新约的基督自由选择了牺牲,照亮了受苦的本真意义。对于愿意与基督担负同一命运的个体而言,就能完全洞识爱与痛苦的必然关系,这里展现出两个层次意义的启示:首先它可以使得个体为自身的痛苦和死亡赋予一个合目的性,从而以一种更加深刻的方式对痛苦和死亡达成谅解;此外,它还在情感状况上启示着个体:痛苦和快乐仅仅只在感官生活的最低情状中才是相互排斥的,越是进入自我深处,两者越是贯通,最终将在基督赋予我们的最纯粹和最高级的爱之牺牲中合一,凝聚,最终达至生命的顶点。
这份救赎的秘密,在舍勒看来,就是“爱”,这爱来自于上帝,已经不再与痛苦、恨恶对等,而是超越、接纳了它们。神的“爱”不需要以世界同样的爱和善作为回报(世界也无力回报)。即便整个世界给予的只是仇恨,神依然爱这个世界,因着耶稣临终的祷告,牺牲的恩典以一种更坚决的姿态、更可畏的力量胜过了现实的罪恶和冷酷无情。
这些道理,简直与尼采哲学一样与中国青年距离遥远,甚至比尼采哲学距离中国青年更远。但“爱”本身有一种魅力,可以呼唤地上的人仰望苍穹,也许中国青年有一天也可以学习到不是终日俯首盯在土地上,而是尝试抬头仰望星空?也许圣经经文中那种陌生的文风和使徒保罗所欲表达的那种悖论的美感能够带给中国青年一种新的视域,或哪怕是对于新的视域的反思兴趣?——“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